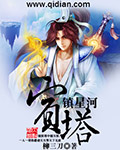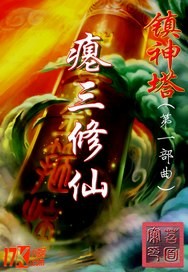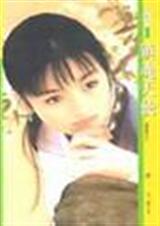南河镇-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窝到的小麦更容易脱粒,等不让晌秋田禾安上后,小麦也就窝得八九不离十了。这时庄稼人便可一心一意来碾打小麦,叫做“碾场”。
渭北的旱原上地广而人稀,几乎每家都留有固定的麦场,叫做“场面”。南河镇一带却恰恰相反,虽是水地却地少人密,因此包括那些大户人家在内,大家都没有固定的场面,而是在那些早熟的大麦收割后临时光场。等碾打完毕,在场面地里种秋庄稼自然是来不及了,于是只能种些生长期短的白菜或者萝卜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那些穷家薄业的小户人家,连临时的场面也没有,他们地少又没牲口,自然是既没能力也没必要再种大麦了。跟大户人家相比,他们那小乌见大乌的麦垛也确实是漂不住劳神光场,他们必须巴结着帮人家碾打完毕,然后再借用人家的场面和牲口,来碾打自家的小麦。
当然也有硬气而不肯巴结别人的,他们采用那更为原始的方式,将那几十捆麦子放在院子里用连枷慢慢地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中人在论及收成时,向来不说今年收了多少多少粮食,而是说今年打了多少多少粮食。用连枷打的如此说,用碌碡碾的也如此说;夏粮如此说,无需碌碡也无需连枷的秋庄稼包谷,竟然也如此说。后人有骡子有马有碌碡,可他们的老先人却没有,历代老先人曾经用过的,也都是连枷。
小麦一般要碾打两遍,第一遍叫做“碾生场”,第二遍叫做“腾秸”。碾场特别是碾生场最怕下白雨,因此碾生场被认为是“紧场活”。生场碾完后意味着大部分麦子已经归仓,因此与“碾生场”相比,“腾秸”就松泛得多了。这时,锄包谷又成了当务之急,包谷锄过两遍后,小麦也大多“腾秸”完毕。
挂上大锄后,在把难得的消闲恩赐给庄稼人的同时,老太爷又将难耐的溽热一块儿降临到人间。知了呐喊着将日头唤出东海,又鼓吵着将日头送下西山。老母鸡的羽翼几乎蜕得精光,身上的鸡皮疙瘩已依稀可见,但它的儿女们却显得异常的活跃,一个个像黄绣球似的,在地上“滚”过来又“滚”过去。无论黄狗黑狗还是花花狗,都是一脸的无奈,尽管都匍匐在潮湿的脚地上,却还是热得将舌头吐得长长的,并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黄牛也好红马也好青骡子也罢,都在不停地甩打着尾巴,有时还舞动着四蹄以驱赶那些嗜血的虻虫。也许正是由于这个需要,它们的尾巴才没有退化而被保留了下来。
成群的绿头苍蝇爬在污物上,贪婪地吮吸着它们的美味和佳肴。人类喜欢的吃食它们喜欢,人们所厌恶的臭屎,它们竟然更喜欢,难怪人人讨厌它们,而且猪嫌狗都不爱了。苍蝇们还意犹未尽,蚊子又迫不及待地弹起了它们那并不悦耳的协奏曲,并从阴暗的角角落落里纷纷起飞,随时袭击着那些赤身裸体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三岁以下的孩子无论男女,身上都脱得赤条条的一条线不挂;成年男人除了搭在肩上的一条黑黢黢的手巾外,充其量只多了一条遮羞挡丑的大裤衩子。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女人,竟然也敢跟男人们一样肆无忌惮的脱去了上衣,两个跟蔫茄子一样的奶头,赤裸裸下垂着。最辛苦的,是那些主妇们,她们得一头扎进那跟蒸笼似的灶屋,为一家大小把生的变成熟的,把凉的变成热的。
夜幕降临前,婆娘女子们便将炕上的席子拉下来,并铺在被她们事先扫得白光白光的,并轻轻撒过一些凉水的院子里,以供全家人歇凉并共进晚餐。
大人们将期望的目光,不时地投向那些柳树的树梢,但纹丝不动的树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他们的期望变为失望。奔波劳累了一天的男人们,只得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于黎明前才进入了梦乡,而主妇们手中的蒲扇,却能奇迹般地由清醒到朦胧一直挥舞到天亮。尽管蒲扇带来的气流并不像期望中的那么凉快,但毕竟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赶开那些伺机就会袭向大人和孩子们的蝇蝇虫虫。
木匠作坊里,济世堂后院的书房中,却只有繁忙和溽热而没有消闲和轻松。在这里,人们手里挥舞着的,是斧头,是毛笔,而不是蒲扇,蒲扇对他们来说,已属奢侈品。
作坊里,木匠们日以继夜地在为学堂赶做桌凳。老木匠跟他的两个儿子正忙着下料,那些初来乍到的徒弟、师弟们只能做些粗活,他们或者用大锯按老木匠“飞”上去的墨线将原木解成板材,或者用小锯将板材再解成线材。已有些经验和功夫、却因尚不老到,还不能独当一面的师兄们都在刨料,将解开的板材或者线材刨平、刨直、刨方,然后再刨光。
所有的手艺行当中,下料是第一道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道工序。铁匠短咧一锤,木匠短咧瓷贼。这句民谚,一语道破了木匠跟铁匠在下料时的基本原则。木匠下料时宜长忌短,长了只须一锯;铁匠则恰恰相反,宜短而忌长,短了只须一锤。下料的木工,对各种木材的性能和特点必须是成竹在胸,对成品各个部件的尺寸和大小也要了如指掌,必须作到能照物下线,能量材使用。
桑木质地光滑手感细腻色泽好看而且弹性极好,挑夫们都会为自己有一根桑木扁担而感到自豪;梨木柔韧,在刀切斧剁下都不会掉渣,枣木质地光滑手感细腻而且瓷实重镇,主妇们都会因有一张梨木案板,一根枣木擀杖或者枣木棒槌而感到骄傲;柏木的油质丰富而耐腐蚀,因有异味,连蜈蚣、穿山甲之类的毒虫都得避而远之,所以老人们也会为自己在百年之后能睡一口柏木棺材,而感到心安理得。桐木因质地轻而且从不变形,所以最适合用来做风箱和锅盖;槐木因硬度高且不易变形,所以是打制水车、旱车,做镢把、锨把的上好材料。当那些槐木节节和槐木块块,被儿女们当柴火塞进灶堂或者炕洞时,老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从火堆里“抢救”出来,并且还会在严厉地指教晚辈们“家有槐,甭当柴”之后,又如获至宝而且得意地自言自语道,“做个镢楔,还是不成问题的。”榆木的特点是柔而韧,缺点是容易变形,所以庄稼人说它是“千年的榆木想娘家”。
木工行当里,技术含量最高的操作是“合缝”,即将两块木板的侧面在刨直刨平后,再用皮胶或者骨胶黏合在一起拼成面板。最难做的家具不是桌子,而是板凳。板凳的卯窍跟榫肩都必须有一定的斜度,以保证它“四腿八蹬”而更加稳当。在这些关键的地方,老木匠都会亲自动手,或者在他的指点下,由即将出师的熟练工来完成。
书房里,陈德润正在给《九章算术》补充着例题和习题,欲使之成为一部更具实用价值的算学教材。孙兰玉在一旁帮他誊写着书稿,还不断地更换着铜盆里的凉水,用蘸湿的手巾来替他擦汗、降温。
远在公元纪年前后的秦汉时期,《九章算术》就已在关中一带广为流传。岁月沧桑,作品没有名字,作者更无从考证。后人因全书共有九个章节,故称之为《九章算术》。其中《方田》一章,涉及到正方形、矩形、梯形、圆形、弓形、三角形和截球体表面积的计算,似乎应相当于后来的《平面几何》;《商功》一章是关于体积的计算,似应属于《立体几何》;《勾股》一章是关于直角三角形的解法,应相当于后来的《平面三角》;顾名思义,《方程》是关于方程以及方程组的解法,并建立了正负数的概念,而《少广》一章,则是关于开平方与开立方的计算,应当属于《代数》;其余诸如《衰分》、《粟米》、《均输》以及《盈不足》,似乎都可以归纳到《算术》的范畴。
老神仙正忙于迎来送往,突然一个身着长衫的人一闪身踱进了济世堂。这人大约有五十挂零的样子,手里拿着一把折扇却并没打开,他既不求医也不问药,似乎对挂在两侧墙壁上的字画更感兴趣。他先踱到右首的墙壁前,见条幅上写有:
病分阴阳表里虚实寒热,须辨症施治。
点着头细细地品味了足足有一袋烟的工夫后,他又踱到了左首的墙壁前,并饶有兴致地玩味起另一条幅:
药有君臣佐使膏丹丸散,应酌情制宜。
就连饱经沧桑的老神仙,一时间也难以琢磨出来人的真实身份,说是达官显贵吧,他却是那样的温良恭谦,而少了些霸气;说是富商大贾吧,他却显得过于朴素,而没有丝毫的荣显;说是文人墨客吧,他却显得气宇轩昂,而看不出些许的迂腐。
老神仙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人,并揣摩着他的确切身份,虽还没弄出个所以然来,但此人决非等闲之辈,却是毋容置疑的了。直到将一茬前来就诊的患者接待完毕后,老神仙才搬过一把椅子说:“客官想必是做古玩生意的,请坐下歇歇脚。”长衫人只说了声“有劳老先生”却并没有就座。他指着条幅上的落款问老神仙说:“这位陈德润陈先生,想必离此不远。敢问能否冒昧一睹风采?”老神仙笑着说:“这有何难?他就在后院,客官请!”言罢,他又向后院打了声招呼说:“德润!有客人。”
说话间俩人已来到后院,掀开竹帘后老神仙将客人让进屋里,并指着正要起身的孙兰玉和陈德润说:“这是小女孙兰玉,这便是小婿陈德润。你们聊。我就不打扰了。”说完后转身就退了出去。孙兰玉出去给客人沏茶,陈德润却对来人说:“这里乱而且热,先生请到客房里用茶。”来人却说:“不必客气。这里挺好。”说着已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顺手拿起孙兰玉正在誊写的书稿,一边翻阅一边连声赞叹说:“好字好字!”在翻过几页后他又惊讶地问陈德润说:“先生这是在修订《格致》?”陈德润也惊讶地回答说:“先生好眼力!”来人先点了点头接着又摇了摇头叹着气说:“只可惜在数千年的科举制度中,国人只知迷恋仕途而尊崇孔孟,这些极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却反而被束之高阁受尽了冷遇。”陈德润更加惊讶地说:“先生所言极是!在下正想将它分门别类加以改编,再作为教材以飨后人。还请先生不吝赐教!”来人又惊又喜地说:“在下亦有此念。不想未及动手,却已被先生捷足先登了。”
“格致”者,“格物致知”之简谓也。“格物”是指事物所遵循的自然规律;“致知”是教而使其知学以致其用也。实乃识物穷理之学,即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属西学。
第十一章周大人屈尊授课 洋
“听口音,府上非湘即楚。敢问先生尊姓,在何处高就?”陈德润试探道。
“先生亦好眼力!舍下湖北宜昌。卑人姓周,在县衙里当差。”来人回答说。
“哦,原来是邹大人。刚才多有怠慢,还望大人鉴谅。”陈德润将“周”字误听为“邹”字了。
“哪里哪里?若非先生提醒,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听说先生在南河兴办新学,新任知县本要亲自前来拜访,无奈初来乍到他公务繁忙一时难以分身,故着卑人送来两样东西聊表寸心。这一千两银子是他的俸银,另外再划三十亩地给学堂作为校产,这是银票和地契,还请先生收好。”从袖筒里拿出银票和地契后,来人对陈德润说。陈德润之误他非但没有介意,还将错就错地点头表示了认可。
“知县大人的美意,陈某受之有愧又却之不恭。烦请大人先代为向父母官致谢,容陈某忙完这一阵后,再到县衙当面致谢。”道听途说中,陈德润已知道在旬日前,有个新县令刚刚到任,却没料到这么快他就知道了自己办学的事,因此有些感动,还有些激动。
“先生不必客气。不知能否赐墨宝一副,卑人回去也好交差?”来人说。
“这。。。。。。只是笔下拙笨又蒙错爱,只好让邹大人见笑了。”说话间陈德润已拿出一个画轴来。来人连忙起身帮着陈德润绽了开来,只见四尺整张的横幅上,遒劲的行草书笔有虚实,字有俯仰,墨有浓淡,行有疏密,落款补白,印章点睛,浑然一体,气象万千。来人不觉眼前一亮,竟于不知不觉中读出声来:(一)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静观天上云卷云舒。
“超凡脱俗又字字珠玑!”来人赞不绝口地说。在小心翼翼地收起画轴后他又接着说道:“先生如此厚礼,不知何以为报?”
“大人言重了。在下正有一事相求,但不知。。。。。。”陈德润欲言又止。
“先生但讲无妨,不必客气!”来人鼓励陈德润道。
“大人如此精通西学,不知能否屈尊为学生授课?”迟疑了一下后,陈德润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想说,却又觉实在难以启齿的心里话。
“原来如此?承蒙先生如此看重,自当不遗余力。只是惟恐不能准时,既误了先生又误了学生。”来人诚挚地说。
“无妨无妨。时间全以大人。”陈德润高兴地说。听到这句话,他似乎比拿到银票和地契时,还要激动。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说罢,来人便起身告辞说:“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见挽留不住,陈德润急忙起身相送。
客人走后老神仙问陈德润说:“此人气度不凡,不知他作何公干?”陈德润回答说:“听说在衙门里当差,我也不便细问。”孙兰玉却说:“以我看,倒像个师爷。”
三个人正猜测揣摩,却见全副戎装的两个青年人,又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
“请问,哪位是陈德润陈先生?”走在前面的青年拱手问道。
“在下便是。两位是。。。。。。”陈德润一边回答一边试探地问道。这两个赳赳武夫,显然不是前来求医问药的。
“西安陆军学堂的王志奇、陕西武备学堂的邓玉昆,拜见先生。”抢前一步,后面的邓玉昆跟王志奇站了个并排。说着,两个人同时向陈德润鞠了一躬。
“噢,原来是新军的两位弟兄。请到客房叙话。”陈德润客气地说。王志奇和邓玉昆也不客气,跟着陈德润便进了客房。
分宾主坐下后,陈德润一面招呼俩人用茶一面问道:“两位远道而来,不知有何见教?”邓玉昆回答说:“不不,我俩虽就读西安,却均为阳都土著。前已久仰先生大名,今又闻先生兴办新学,故冒昧前来讨扰。”王志奇又接着说道:“既是新学,想必要开设有军体课?”陈德润颇为惊讶地问:“军体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