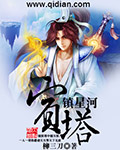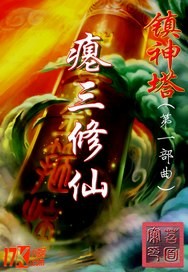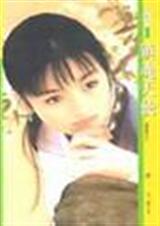南河镇-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洪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成仇(洪承畴)
史书留名,虽未成功终可法(史可法)
洪承畴与史可法均为明末重臣。在战败被俘后,史可法宁死不屈成为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而洪承畴却投敌变节沦为个个唾骂的民族败类。
借古喻今,上联托洪承畴之名以瓦解清军的军心;爱屋及乌,下联借褒扬史可法以鼓舞民军的斗志。
范紫东是著名的剧作家,在陕西享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美誉。为弘扬爱国精神以激发军民的士气,县剧团还给革命军的全体官兵们,连夜演出了范紫东自编自导的秦腔历史剧《史可法》。“史剧”生动地再现了民族英雄为抗击清军,与扬州城玉石俱焚的历史画卷。英雄的形象,悲壮的场面,使全体军民无不深受感动。军民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誓死保卫乾城,誓与清军血战到底的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从傍晚到翌日清晨,“史剧”连续滚动演出了四个场次,阵阵掌声雷鸣,场场观众爆满,誓与乾城共存亡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彻夜不息。天,被感动了,竟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地,也被感动了,竟微微地抖动了起来。
恽升的中军帐也在随之战栗。一阵夜风突然袭了进来,在他的军帐中旋转着移动着。旋转的半径越来越小,强度却越来越大,旋风的轴线,也沿着螺旋线一直移动到他的公案前。放在公案上的一纸公文,竟随风旋了起来。那不是普通的来往公文,而升允不止一次为之三叩九拜过的圣旨;那不是给他加官进爵的圣旨,而是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的诏书。又惊又疑,升允再也睡不着了,他不得不陪着城中军民,坐等天明。
混进城中的清军探子,竟也为剧情所吸引,为观众所感染。朦胧的夜色中他们皂白难分,夹杂在其中的百姓,竟被他们当成了革命军;用锅墨抹黑后搭在城墙上的木头,又被他们误以为革命军架上去的大炮。每场演出结束后,都有探子鬼鬼祟祟的夹带在百姓中混出城去,守城的革命军更是装聋作哑,稍加盘问后便予以放行。
听说观看演出的革命军,每场都在万人以上;而架设在城墙上的大炮,也不下百门。有的口径,甚至比把把老碗还要粗。恽升闻报,不觉心里暗暗吃惊。
第二天一大早,站在姑婆陵上远远望去,发现乾陵县的城墙在一夜之间,竟奇迹般长高了三尺,升允连连顿着足大呼上当。他原想趁革命军立足未稳连夜攻城,不想却为范紫东跟张云山布下的疑兵所惑,而未敢轻举妄动。昨晚的《史剧》既鼓舞了士气,又迷惑了敌人,同时也为张云山的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乾城的城头上,革命军严阵以待,终于站稳了脚跟。
错过战机,恽升不禁恼羞成怒,恨不能喝口凉水将乾城一口吞了下去。他一声令下,清军便像爆发的山洪一样漫山遍野而来,又跟出笼的猛兽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乾城。一阵人声鼎沸马嘶咴咴喇叭呜咽战鼓咚咚旌旗猎猎刀枪铿锵之后,只见尘土飞扬狼烟蔽日剑拔弩张刀枪林立,乾城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犯之敌,革命军更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他们人人摩拳个个擦掌士兵争前将官恐后。百姓们更不甘示弱,上自六旬老人下至八岁顽童,男的都武装以镢把锄头,里三层外三层地防守于城头,女的也忙着送水送饭,往来穿梭于大街小巷。其声威与拼命的架势,亦不亚于清军。
震耳欲聋的三通炮响后,革命军分三路杀出,其势锐不可挡。清军倒是先乱了阵脚,但贼军毕竟势大,在退却了一阵后他们不但稳住了阵脚,还凭着人多势众,手里又有快枪利炮,很快便向只有大刀长矛鸟枪火铳的革命军反扑了过来。终因伤亡惨重,革命军抵挡不住而开始节节败退,有的甚至被分割包围。在紧急关头,侦探营管带王士奇虽身受重伤,却临危不惧并大声疾呼曰:“临阵脱逃,实乃革命军人之奇耻大辱!真丈夫者,跟我上!”说罢他冲锋陷阵身先士卒,连着砍倒了七八个贼兵。受到鼓舞,革命军又返身奋勇拼杀,跟清军展开了拉锯战。
当双方正在酣战,直杀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东南方向上喊杀震天。清军顿时大乱,像潮水般的向北溃退而去。革命军士气复振,在王士奇的带领下正要趁势掩杀,不料清军却已鸣金收兵。正惋惜时,却又见一彪人马旋风般的刮到城下,为首的三个壮士皆虎背熊腰,大旗上还绣有一个斗大的“项”字。不知是敌是友王士奇正待接战,却见为首的三个壮士已滚鞍下马。
“哥老会的项氏兄弟前来投奔革命,投奔大哥张云山。”三个人同时抱着拳异口同声地说。不知是真是假王士奇正在犹豫,张云山却已经闻信赶了过来:“啊呀,是项大胆!”说着张云山也翻身下马,并与其中一个紧紧地搂在了一起。
被叫做项大胆的叫项志山。项志山跟张云山同是哥老会的弟兄,因为人仗义豪爽敢作敢为又排行老大,所以被哥老会的弟兄们称为项大胆。项志山是哥老会在渭北一带的领袖人物,为此还被清政府逮捕和关押过。听说张云山跟清军酣战于乾城,项志山便与他二弟项志仁和三弟项志义,带着千余名哥老会的弟兄前来助战。在两军激战,且战况越来越不利的紧急关头,多亏项氏兄弟及时赶到,这才使革命军转危为安又转败为胜。
进城后,范紫东跟张云山立即吩咐设宴为项氏兄弟接风、洗尘、庆功。宴会上项氏兄弟慷慨请缨要求趁热打铁乘胜出击,范紫东却考虑到清军虽败但元气未伤,而革命军四面受敌仍处劣势,于是建议以守为攻挫其锐气。觉得双方都有道理张云山正踌躇不决,却正好接到西路失利岐山失守的消息,于是他当机立断,将项氏所部改编为革命军项字标,命项志山为标统,项志仁跟项志义分别任营长,并立即起程驰援并收复岐山。按范紫东的意见,张云山以静制动坐镇乾城牵制升允,以减轻革命军在其它两路上的压力。
乾城城高池深,加上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协力,致清军久久不能得逞。强攻不下,清军挖地道,诈降等种种伎俩,又被革命军及时识破而以失败告终,升允这个老狐狸不得不改弦更张了。他决定暂时放弃乾城这块久克不下,弃之又觉可惜的“鸡肋”,在留少量兵力命马安良与张云山虚与周旋后,他自己则带领重兵,连夜将近在咫尺昭陵县城团团围定。
恽升的阴谋,终于得逞了。昭陵县城可以说在一夜之间便陷落了,也可以说在两年后才陷落了。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七日夜晚,是一个特殊的夜晚,这个夜晚的前半夜还是宣统三年的腊月三十除夕,而后半夜却已是民国元年的正月初一凌晨。
乾陵县城久攻不下,昭陵县城却唾手可得。其主观原因,自然是昭陵县守军忙于过年而疏于防范;其客观原因,是由于这两个县城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
偌大的一个昭陵县,何以竟将县城建在了与乾城的交界上?对此,多年来竟无一人能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于是民间便演绎出一段轶闻趣事来。
传说中两县因边界久定不下,在翻来覆去的磋商中,昭陵县的老爷出了一个看似公平,但实际上却是很损的主意。他们约定在某日三更时分,各自在对方代表的监督下从自己的衙门出发,并沿事前商定的路线相向而行,俩人在哪儿碰面,哪儿便是县界。昭陵县的老爷原以为对方肯定不会接受,没想到人家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昭陵县的老爷心中窃喜,他自恃年轻,又欺对方的腿脚有些不便,因此根本不把乾陵县的老爷放在眼里。衙役们从二更一直叫到五更,昭陵县的老爷却还是烂醉如泥沉睡不醒。见乾陵县的老爷已经坐在了自家的大堂上,昭陵县的衙役们索性不再叫了。这一觉昭陵县的老爷直睡到晌午端,这才打着哈欠又伸着懒腰醒了过来。
“老爷,乾陵县的老爷,已经在大堂等候多时了。”昭陵县的衙役们抱怨道。
“乾陵县的老爷?等我,他等我有得何事?”昭陵县的老爷,不解地问道。他早已将昨天约好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乾陵县的老爷腿虽瘸,脑子却一点也不缺。深知处于劣势他丝毫不敢大意,虽然想到了“龟兔赛跑”的典故,也想到了“笨雀先飞”的俚语,但他却信守诺言并没有偷偷地“先飞”,而是一更起床二更用饭,然后一直坐到三更,才准时的动的身了。唯恐有负全县父老,一路上他一瘸一拐跌跤爬坡地向前赶着。一直没见到对方的影子他更加着急,等马不停蹄地赶到昭陵县的大堂时,这才知道对方还在做着美梦。
乾陵县的老爷,是一个宽宏大量的长者。为不使昭陵县的老爷过于难堪,他没有坚持按约定将县界划在昭陵县衙的大堂上,而是主动让一步划在了城外。昭陵县的老爷无地自容羞愧难当,从此跟乾陵县的老爷一样,也变得勤政爱民起来。
既得陇,又望蜀。踌躇满志,恽升坐镇昭陵县,虎视着阳都县,又垂涎着西安省。西安古时又叫长安。长安者,长治久安也。恽升以为,大清原本就不该建都北京,而应建都长安。若是建都长安,大清帝国也许就能长治而久安了。
西周就是建都长安才兴起的,后来虽有周幽王因“烽火戏诸侯”而出过乱子,但天下却还不至于因此而异姓,而东迁后不久,就分裂成春秋五霸,又继之以战国七雄直至亡国。西汉也是在长安兴起的,期间虽有外戚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却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而东迁后却分裂为十八路诸侯,又继之以三国鼎立直至灭种。庚子年八国联军都打进了北京,但却打不到不了长安。光绪皇帝跟两宫太后一到长安,不是就没事了么?
唇亡则齿寒,作为西安门户,阳都既不能丢,却又无险可守。多亏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阳都知事陈德润早有提防。在他的授意下,城防营官邓玉昆带着为数不多的队伍,已敦促着沿途的百姓们坚壁清野,凡能吃的东西,都被藏进了地窖,所有的水井中,都被底朝上地投入了背笼。百姓们扶老携幼,也被有序地撤到阳都城内与渭水南岸。
城内,东大街的城隍庙,西大街的东岳庙,北大街的关帝庙,南大街的萧何庙,西道巷的三官庙,县门巷的菩萨庙,财神庙巷的财神庙,马王庙巷的马王庙,甜水井巷的吕祖庙,仪凤街的药王庙和安国寺,以及渭水南岸东张村的金佛寺,马家寨的千佛寺,曹家寨的兴国寺,河西堡的丰盛寺,王道村的弘济院,段家堡的杨村庙,河东堡的老爷庙等,已被难民们挤得满满当当。
南河实业学堂也已改为临时医院,收治着从昭陵前线溃退下来伤病员。老神仙和戴维夫妇带着医护班的学生们,不分黑明昼夜地穿梭教室与宿舍之间,为伤员们手术、换药、包扎。。。。。。
桥头面馆已经被迫歇业。谢铁成那已关门多时的铁匠铺子里,又风箱呼呼炉火熊熊锤声叮当火星四溅,正在为前线连夜打制和修理着那些冷兵器。
木匠作坊里,老木匠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与徒弟们,正在修补着那些已经被流弹打得窟窿眼睛的船只。
千年古渡的南北码头上,更是灯火通明,大小船只往来穿梭,低沉而短促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包括七十子兄弟在内,所有的船工们,都日以继夜地给前线运送着队伍、粮草、军械和辎重。
百姓们刚撤离完毕,清军已尾随而至,并在头道原跟二道原之间安营下寨,将阳都古城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团团围定。南河镇成了阳都古城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惟一的水上通道,也成了古城惟一的大后方。全民皆兵,男女老少总共动员,大刀、梭镖、铡刃、铁叉和顶门杠子,甚至连烧火棍也都成了武器。面对穷凶极恶的清军,所有的南河镇人,所有的阳都县人,空前地拧成了一股,团结得像一个人。
埋锅造饭时,清军这才发现不但找不到一粒粮食,就连一桶水,也打不上来。兵无粮自散,已无心恋战的清军,在佯攻了一阵后便拔寨而去。听说后升允不由大怒。第二天他亲自督战,让战马驮着粮食士兵挑着饮水,又一路卷土重来。粮食还好说,一担水连洒带漏还不到中途,水桶却早已见底。
就在升允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时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关于南北议和的消息,又传了过来。
武昌起义爆发时,宣统皇帝溥仪还是个只有六岁孩子。为了对付革命,他父亲摄政王载丰不得不重新起用两年前刚被他罢免,正赋闲在家的袁世凯,并授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实职。袁世凯毕竟不是升允,大权在握后他拥兵自重,不但没有朝着溥仪山呼万岁,而且还重演了《白逼宫》,迫使六岁的万岁爷退出了皇位。袁世凯打着拥护共和的幌子,又以迫使清帝退位而居功自傲,以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非他袁某人莫能属焉。
只将身一摇,袁世凯就由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变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大总统前冠以“临时”二字,使袁世凯颇觉遗憾,因此不久便被他去掉了。自己总不能扇自己的嘴巴,袁世凯以清廷内阁总理和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双重身份,下令命清军和革命军握手言和。这场政治交易,就是所谓的“南北议和”。
第十三章范紫东兵不厌诈 陈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国家,竟出任了四个水火不能相容的显赫职务。除了袁世凯,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怕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岑椿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其他人姑且不说,而用“不学有术”四个字作为对袁世凯评价,恐怕是最贴切不过,亦最精当不过的了。
自古以和为贵。袁世凯“南北议和”主张,最初还真的赢得了新旧两派的一致的拥护。不愿再同室操戈手足相残的人们,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并握手言欢言归于好。
当然也有不买账的。升允就是个典型,他破口大骂袁世凯并拒不议和,还私藏主子的退位诏书,企图使这个已经化为孤魂野鬼的政权,有朝一日能奇迹般的死灰复燃,同时还梦想着在大西北为其建立一个小朝廷。
困兽犹斗。虽黔驴计穷,升允却还是利用北原上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地负隅顽抗着。他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