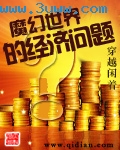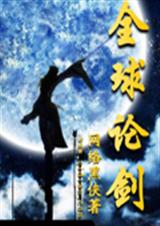经济学林论剑-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我们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错的,经济学必须重建!因为,递减规律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少了这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要倒塌。可以将递减规律修正为:如果是周期性或连续性发生的个体商品或劳务消费,不论这种消费品是生活必需品还是非生活必需品(包括烟酒、鸦片等“上瘾品”),消费者得自其中的边际效用必定递减。
什么叫边际效用?就是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品,带来消费者的效用的增加量。比如说,在你口渴的时候,你愿意花2元钱买一杯矿泉水,这说明你对这杯水做出了值2元钱的主观评价(可看做它可以给你带来2元钱的效用)。当你喝下这杯水之后,口不那么渴了,于是现在你只愿意以1元钱买第二杯水,即它只给你带来1元钱的效用,这1元钱的效用,就是第二杯水的边际效用。第二杯水下肚,你已经不口渴了,也不愿花钱买水了,除非第三杯水白送给你喝。于是第三杯水给你的效用是0,即第三杯水的边际效用是0。第三杯水下肚,你的肚子已经胀了,如果还要你喝第四杯,你不但不觉得爽,反而觉得难受,这第四杯水给你带来的就是负效用,它的边际效用是负的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一种商品的消费量越多,那么,这种商品对于他的边际效用是逐渐减少的,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以下简称“递减律”)。
“上瘾品”是否也遵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茅于轼先生在题为《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的文章中称:“收益递减律无法用任何逻辑的方法加以证明,所以它只能当作经济学中的一条公理被接受。”但他同时表示:“吸毒就接近于收益递增”。然而,“公理”是没有例外的,就如茅先生自己所说,“所谓公理,就是一种假定,从来没有被任何事实所否定,虽然它不能用逻辑方法来证明,却能广泛地被接受。” 茅先生的观点自相矛盾。汪丁丁先生在题为《为什么“边际效用递减”?》的文章中分析认为,可以“上瘾”的消费品,边际效用是递增的,如吸毒和酗酒。他把这些情况处理在“不正常消费品”之列。
将吸毒等作为“例外”,这是国内外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看法。但是,按照这些学者的逻辑,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类似的“例外”。如A先生喜欢收藏字画,对他而言,搜罗的字画多多益善;同理,B先生喜欢集邮,C先生喜欢游泳,D先生喜欢打麻将……这些人的消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嗜好某物品或消费如命,按照茅、汪等先生的逻辑,这些情形都应该是边际效用递增的。但是,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我们就不得不推论如下:要么是这些学者(包括茅、汪等先生)的观点错了,要么是递减律错了。
如果我们认为递减律是错的,这将出现严重的后果:经济学必须重建!因为,递减律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少了这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要倒塌。因为没有它,就不能推导出需求、供给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就不能描述市场经济发生作用的机制,就无法构筑整个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但是,我觉得可以得出这个判断——经济学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与完善,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已经趋于完美了,它不可能错,它赖以建立的基石也不大可能错。当然,我的这个论断有些武断。
看来,茅、汪等学者的推导可能存在缺陷。缺陷在哪里?我在这里先给出我认为正确的答案:他们的推导缺陷在于对递减律无界限的应用,或者说是对该定律的边界或内涵实行了没有界定的应用。
翻阅了大量的海外经济学著作,我发现那些学者关于递减律的讨论,都是用形式逻辑中的归纳论证法进行推演的(茅先生认为该规律无法证明,显然是不严密的)。他们认为该规律需要考虑前提条件(茅先生将它作为公理,也是不严密的)。如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在这一规律之中有一个暗含的条件,应当加以说明。就是我们假定,不容许这期间有时间使消费者自己在性格和爱好上发生任何变化。”这其实是假定人的偏好不变。
马歇尔的限定,尽管解决了前面所提到的“例外”可能带来的导致递减律破产,进而解决了可能使整个经济学大厦倒塌的恶果,但是,它使得递减律不切合实际,很武断,有些玩弄逻辑游戏的味道。因为,人的偏好必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是事实。作为一条“规律”,如果同诸多的“事实”相违背,无法真正解释现象,则该规律必定是伪规律或者说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到底如何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做出前提限定?这可以从我们的消费品分析得出结论。
尽管消费品包罗万象,但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生活必需品,如柴、米、油、盐等;非生活必需品,即在各种生活必需品得到保障之后出现的,如各种装饰品或炫耀性商品等。
——生活必需品。经验表明,就餐时,如果满桌子都是某一种菜,我们会感到厌烦。所以,比较理想的是,菜肴必须是荤素搭配。前者符合递减律,“理想状态”不符合递减律。为什么?前者是个体,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后者是总体,即几种菜的效用的加总,所以消费的品种增加时,加总的或者消费者所得到的效用是增加的。也就是说,存在总体效用与个体效用的区分。所以,在需求的任何一个周期中,同类和等量的一定数量的消费品所带来的效用的每一次追加,必然被估算得比前一次低。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上瘾品”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2)
但就个体物品而言,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以吃烧饼为例,如果烧饼的材质发生了变化,那么其边际效用未必递减了。如果将人的一生纳入该规律的视野,那么,对于人的一生而言,从出生到死亡,第一口烧饼的效用最大,以后递减,直到死亡前的最后一口烧饼,效用最小。如果在人生中途,出现饥饿状况,而且到了饥饿的极限,如果有烧饼提供就能存活,没有烧饼必定死亡,这时,只为其提供了一口烧饼,人照样死了,这最后的一口烧饼的效用,到底是最大还是最小?所以,要使递减律得以成立,还必须进行限定:时间一定,产品同质。
——非生活必需品。人类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一般表现为多样性和广延性。所谓多样性,是指人们对该类产品的需求,自始就是富于变化的,一种需求会引致出另一种需求;所谓广延性,指的是它们往往包含着广阔的目标,其范围又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而扩大。看来,这种需求似乎是无限的,而且其边际效用可能不是递减的(中外学者提出的“例外”多属于这类产品)。比如说,一位先生嗜画如命,一见到好画(名画)便不惜花费极高的代价(或者说是一切代价)得到它。而现实中,这种人比比皆是。他们的嗜好成了一种怪癖,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行为,似乎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他每得到一幅画,都不会减弱他的强烈的愿望,相反,刺激了他的新的欲望。这种现象是否推翻了递减律?如果毫无变化地重复同样的行为(完全相同,既无扩展,也无变化),则其结果也是必然走向厌烦或厌恶。因为,这里同样存在总体效用与个体效用的区分:具体到某幅画,比如说唐寅的仕女图,如果同样的一幅,则任何一个字画收藏家都会异常兴奋。但如果某收藏家再拥有同样的一幅画,则兴奋的感觉将削弱,如此增加,直到N幅(N取值在3到无穷大),则对他来讲,唐寅的这幅画可能连废纸都不如了。我想,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收藏家手头有两幅同样的名画,会毁掉其中的一幅。
收藏家之所以欲望无穷,是因为他已经获得的画或者还没有获得的画,是不同的,各幅画给他带来的效用加总,就是他的总效用,而“每个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即使拿汪丁丁先生所列举的酒的例子,同样可以得出一样的结论。在炎热的夏天,喝一杯冰啤酒会使你感到神清气爽,舒服极了。喝第二杯,感觉也不错;喝第三杯、第四杯甚至更多杯,感觉会怎样?如果第二杯啤酒给你的满足度跟第一杯一样的话,我们说边际效用恒定。但是,第三、第四、第五甚至第N杯啤酒,给你的满足度,跟上一杯相比如何呢?满足度或者效用,还跟上一杯一样吗?显然,良好感觉会逐步降低,若觉得不胜酒力了,说明边际效用达到了零;如果再喝,则会醉酒、呕吐,那么,边际效用就是负的了。
同理,毒品的消费也遵循这个规律。如果在某一时间,吸毒带来的效用,抽第一口必定快感强烈,抽第二口的感觉次之,依次类推到抽第N口时,则达到均衡点,无感觉了,再增加则吸毒者必定产生难受或其他不良感觉,也就是说,吸毒带来的效用成了负的了。当然,吸毒这个事例的推导,是我凭空想象的。毕竟,我没有吸过毒。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修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如果是周期性或连续性发生的个体商品或劳务消费,不论这种消费品是否为生活必需品或非生活必需品(包括烟酒、毒品等“上瘾品”),消费者得自其中的边际效用必定递减。
2002年9月20日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1)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兼与科斯、茅于轼等先生商榷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一些学者认为:“人不过是一条用绳子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狗的绳子的长度。”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制度决定论”,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现象就无法获得科学的解释。
有一家西方刊物称,科斯及制度学派说出了一个道理,即在既定的制度下面,“每个人不过是一条用绳子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卢周来:《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三则)》,载《书屋》,2002年第4期)。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着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也决定了人的行为的选择余地。一只最大限度地追求自由的狗,总会使自己的活动半径尽可能地增大,但是,它的活动半径决定于绳子的长度。而在既定的制度下,人的行为选择也总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于是,科斯及其追随者认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制度设置,也就是研究“拴狗的绳子”。
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这种观点颇有市场。一些学者甚至对这个观点做出了进一步的拓展。例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在题为《中国改革的制度观》的文章中称:“经济制度正像地心引力,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但它们又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并不感觉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在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之前,人类之中并没有谁说出过地心引力的存在。现在经济学家需要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即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这段话可以看做“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的翻版。
不可否认,多数人是在一定制度下选择行为的。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下,人类的行为截然不同,比如腐败现象在很多国家很严重,但在新加坡较少,这并不是因为新加坡的公务员素质高,而是因为其有一套完善的游戏规则(制度)——“高薪养廉”(很多人到目前依然存在误解,以为给了高薪,公务员就可能开始清廉了),也就是说,公务员的待遇很好,从工资待遇到其他种种福利(涵盖其家庭成员)都非常优厚,没有必要去受贿。但是,一旦某个公务员受贿了,这些待遇全都不存在了,甚至他一生都难以翻身。邓小平也曾说过,好的制度,坏人也会变成好人;坏的制度,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但是,上面“拴狗”例子的分析还不够完善。第一,我们不能忽视“树”及其周围环境的因素,否则,你将“狗”往哪里“拴”?“狗”在哪里立足与行动?“树”及其周围环境,可以看做是人所依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等);其次,“绳子”并不等价于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表述是:“人的行为无不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进行最优化选择”,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约束条件”,除了制度,还应该包括信息、生存能力、智慧、时间等。比如说,“囚徒困境”为什么会出现?简而言之,就是个体在约束条件下做出的最优化选择的结果。而这个约束条件,除了检察官所规定的外,就是隐蔽在现象后面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对方将选择的策略,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又如在战国时期,齐威王喜好同臣子赛马,大将田忌却屡赛屡败。后来,孙膑发现田忌用马不妥,于是出谋略:用田忌的三等马同齐威王的一等马比赛,用一等马同齐威王的二等马比赛,用二等马同齐威王的三等马比赛,结果三局两胜。田忌的胜利,是因为他知道了双方赛马脚力的情况以及齐威王的策略这个重要的信息。
第二,如果我们单纯地强调制度的作用,或者说坚持“制度决定论”,那么,现实世界中大量的事实就无法获得解释。制度(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我也一直强调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制度只不过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函数中的主要变量之一,但不是主要变量的全部。例如,最近美国众多大公司不断曝出财务造假丑闻,就不是单纯的制度问题。美国人讲究透明、专业、效率、诚信,企业主管对此四大原则信守不渝,视为教条,这在世界是出了名的。美国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及查账制度,被评为全球典范。但是众多大公司和相关机构还是勾结起来造假。我在《谁导演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载《羊城晚报》,2002年8月10日)中分析过,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超越游戏规则行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利润率高达300%,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