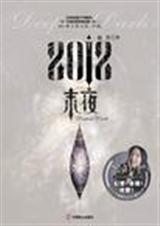灵异手记12亡者低语by那多-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那多
序
本来是没有这个序的。
一切了结之后,我用半自传的方式写下这些文字,把遭遇的事情理清脉络。我愿意花这么大的力气写下十几万字,也有另一层不太愿意提及的意图:当某天我因为某种原因突然消失,好有别人知道,在我身上曾发生过的这许多事情。
真的会突然消失吗?谁知道呢,事情总有万一。如果愿意,你们读到这儿的时候,可以打电话到上海晨星报社,看看还有没有一个叫那多的记者活着。
既然是根据回忆写就,我便总是按照事情的发展按部就班地叙述。这往往并没有问题,但写完这篇手记之后,我重读一遍,发现如果是不了解我于二零零五年经历的太岁事件的阅读者,会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所以我加了这一小段,作为背景补充。
当年的事情,是这样的。
起于一场急性传染病,发病的小区被严密隔离,禁止进出。这种罕见的病叫范氏症,表现为患者体内内脏器官急速膨胀,直到挤爆患者身体,死亡率百分之百。这种病本来只有蟾蜍才会得,病毒变异后危及人类,一直研究此病的海勒国际派出医疗小组,帮助上海市政府控制疫情。
当时我是唯一被允许进入小区的记者,与医疗小组也有很多接触。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我爱上了医疗小组的成员何夕,也发现范氏症的本质是内脏被激活,试图离开宿主,获得属于自己的真正生命。极少数内脏在破体而出之后,可以成功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变成俗称的“太岁”。
通常太岁的生命力虽然让人咋舌,但并不会有智力,但是,当一个由人的大脑突变成的太岁出现时,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脑太岁希望所有的人类都染上范氏症病毒死去,这样它就会有更多的同类,不再孤单。散播病毒的最后关头,脑太岁依附控制的傀儡被击毙,但脑太岁并没有死,留书“等待亡者归来”六个字后,逃之夭夭。
在那之后的这许多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脑太岁的消息。
直到……
楔子
我在深夜醒来,身上是腻腻的汗。
黑暗里睁眼看了会儿,手撑着半坐起来,觉得全身酸软,没有一点力气。
通常我的睡眠都很好,沾了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如果没人打扰,甚至可以直睡到中午。小时候看动画片,主人公希曼有豹的速度熊的力量,我想我拥有的能力是猪的睡眠。
可偶然也有像现在这样的时候。
不一定是做了什么恶梦,只是突然地醒来,然后短时间里无法入眠。
我知道,这是一路走来,留下的痕迹。在身体里,在魂灵深处。那些经历的诡奇事件,这世界的零星真面目,一桩桩一件件叠起来。我曾以为天大的事过了就过了,惊涛骇浪全化为事后谈资,但不是,它们的影响一直都在。
这就是知道真相的代价吧。
我打开床灯,下床,走到书橱前。床灯发着亮黄色的光,但毕竟只是台灯,照到书橱的时候,已经黯淡了,阴影处处。
书橱里没有书,放着的是这些年来的收藏。我不愿把这些藏品放在客厅里,因为它们有点特殊。
比如放在最上层的一把青铜酒壶和两个青铜杯。这酒器造型高古,汉时式样。实际上,还真是东汉末的东西,曾是曹操的酒具。或许曹孟德吟唱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时候,就把着此盏。这是“幽灵旗”事件后,我从充满了自杀暗示符号的曹操墓里生还,顺手取的纪念品。当时从墓里出来的另两人,一个取了《孟德心书》,一个取了一卷竹简,一柄千年未锈的长剑,一盏黄玉酒壶。
青铜酒具旁,放着一截锈迹斑斑的铁管子。看起来这管子一点都不出奇,其实它并不是人工制品。这是我从青海德令哈市白公山脚捡回来的,一株金属植物的小段枝节。当时它的母体曾令所有知情者震恐,担心其对金属分子的富集力增加下去,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一场核爆过后,母体钻入地心,在她把地心金属都吸收完之前,也许再也不会出来了。
整个书橱里唯一能和书稍沾边的,是几本黑色硬面抄。里面是另一个那多写的“那多手记”。当初通过各种古怪渠道拿到硬面抄的时候,我以为是某个同名同姓者写的短篇小说,实际上,这是另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我”在消逝之前,用以向“年”复仇的武器。听起来有点古怪是吧,“年”,这是一种生活在时间维度中的生物,独立于我们的生物学进化谱系之外的怪兽。
差不多每一次的冒险,我都会取一件纪念品放在这个书橱里。每每回顾时,不禁感叹在经历了这些之后,竟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也不总是如此,多年前那次人洞之行,就没有来得及带回任何东西。路云某次看见我这个书橱,便问需不需要她回一次人洞,取件纪念品放进来,被我立刻拒绝。那洞里只有累累人骨,我不想在卧室里摆这种东西。
书橱第二排上有一个大玻璃罐子,我盯着它多看了几眼。玻璃罐里的无色液体是福尔马林,泡着的褐色物就是民间俗称的太岁。传说中太岁是不死的,割掉一块会长回来,有日割一肉,永食不尽的说法。而今的生物学家对它研究不多,有的认为这是种罕见的菌类生命。
但我知道太岁究竟是什么东西。
2005年上海的某个小区曾被完全封闭了几个月,因为一种无药可救的范氏症在小区内蔓延。感染者的内脏代谢会在短时间内上升到极可怕的程度,疯狂汲取营养变巨,最后挤爆胸腹腔。这种病的本质,是内脏突变成独立生物,开始新一轮成长并试图突破人类躯壳的束缚。就像寄生蝇的幼虫在松毛虫的卵里成长,等到幼虫长成破卵而出,宿主当然就死了。
基因学界曾有过讨论,人是否仅仅作为基因的载体而存在?而患了范氏症的人,是确确实实成了内脏的载体,或者说,太岁的载体。当然,在那些变巨把宿主撑爆的内脏中,仅有极少数成为了太岁,多数在人死后不久也失去了活性。
泡在密封罐里的太岁,就来自四年前的那个小区。它曾是人肺叶的一部份,被何夕切了一小块给我,浸在福尔马林里密封着,冻结了体细胞的再生。但太岁的生命力实在太强,我怀疑现在如果打碎玻璃罐让它和外界接触,没准依然可以慢慢长大。
书橱的所有陈列品里,太岁是特殊的。在我看见其它的收藏品时,或感慨或唏嘘,有对那段历险的缅怀,有对这世界真面目的叹息。但这太岁,却是横在我心头的刺。
引发2005年那场危机的原凶,就是一个太岁。和其它普通太岁的差异之处在于,它竟然是由人类大脑突变而成的,拥有高度的智力。更为可怕的,是这个太岁可以吸附在人身上,连通神经突触,从而控制寄生体的一言一行。
当时这个太岁试图在上海散播范氏症病毒,不惜令千万人死去,以产生更多的同类。幸好最后关头,被两枪击毙。然而所有人都忽略了,其实被击毙的只是太岁的宿主,子弹并未击中吸附在宿主肚子上的太岁本身。
最终的结果,是市局法医解剖室内,宿主尸体上被解剖刀刻下了“等待亡者归来”六个字,而原本吸附在尸体腹部的太岁连同法医,消失无踪。
这些年来,再没有“亡者”的消息,但我心里总是觉得,也许下一刻,它就会带着无穷的恐怖归来。
我盯着阴影里的玻璃罐,其中的太岁切片若隐若现。
我心头的阴霾越来越重,却有一大半,和或许会在未来某日归来的“亡者”无关。
是因为昨天何夕的不适。
自打何夕从瑞士归来,摇身一变成为法医,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几乎没生过病。有回晚饭时我见她左手上有道淡淡的疤,先前从未见过,随口问起,竟是当天下午在解剖室里不小心割伤的。而三个小时后我送她回家时,那疤已完全褪掉了。
可是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不舒服一次。便如昨晚,晚餐吃到一半,她就突地停筷,两颊潮红,额头上渗出细汗。然后,就要我送她回去。
她从不去医院。她明白这是为什么,我隐约也知道,所以更忧虑。当年她感染范氏病毒后独自离开,一年后她奇迹般生还归来,具体发生了些什么,这是她的秘密。我很注意不侵入她的领地,直到某一天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我躺回床上。
她什么时候才会告诉我呢,我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想。
或许,我一直以来的做法,有些问题?
有的时候,灵光一闪,换了个思路,才会意识到从前走了死胡同钻了牛角尖。
我向来尊重别人的秘密,越是亲密的人,越是注意不要越界。所以每次何夕要求独处,独自熬过或者用某种方式渡过那段不适期时,我都默默把她送到家门口,然后离开。
但任何女人,再独立再硬气的女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希望能有可依靠的男人在身边的吧。其实男人也是这样,只是我们不说而已。
而秘密,当属于一个人的秘密被另一个人分享时,彼此的关系,难道不会变得更密不可分吗?
只要你能够承担伴随着秘密而来的责任。
我能承担吗?这是个不需要思考就能有答案的问题。
我几乎立刻要打何夕的电话,然后反应过来,这还是半夜里。
我居然愚蠢至此,到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
我的心情顺畅起来,不知不觉中入眠。
第一章 第一个消失者
醒来的时候,手机一边响一边震,在床头柜上缓慢移动。接听前我看了眼时间,十点二十。
是部主任宗而。
“那多啊,钓鱼案的事情,你说我们是不是跟进一下?”他用商量的口气问我。
近几年,上海最最著名的社会事件,除了倒楼案外,就得数这次的钓鱼案了。城管部门放倒勾假装乘客吊黑车,在我这个跑老了社会新闻的记者来看,算是司空见惯毫不令人吃惊的手段了。如果不是这一次被勾上的司机觉得太冤断指明志,传到网上举国哗然,恐怕又要像从前那样不了了之。
政府是个庞然大物,要推动任何一个角落的改革,都需要强大的力量。就如多年前孙志刚之死促使收容制度改革一样。事实上,现在民众呼吁的停止“钓鱼”还压根称不上什么改革,莫说那些好心让路人搭便车的无辜司机被强行拔车钥匙罚款,就算真是无证运营的黑车司机,依法都是不能用放倒勾的方式取证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应该怎样和现实怎样,常常都有很大的差距。
这些天来,因为钓鱼案,全国大大小小媒体的社会口记者,全汇集到了上海。不过相对来说,本地媒体都比较“克制”,上海的新闻审查是著了名的“周到”,管不了别地的媒体来采访,本地的媒体还是管得住的。其实不单上海,就算是以尖锐闻名的《南方周末》,在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时都不免束手束脚。
所以听见宗而这么说,我有些吃惊。
宗而当然知道我在想什么,电话那头苦笑道:“这么大的新闻,多少媒体都在报道,市里再怎么捂也是白搭,这两天口气已经松动了。你看吧,过不了几天上海那几张大报也得开始跟进深度报道了,我们小报,要动得比他们快一点。还有啊,你是社会版的主笔,也不能总不写时评,就写个钓鱼案的评论吧,尺度……你是老记者,知道的啰。”
有一阵平媒都兴首席记者首席编辑,现在又多了个主笔衔,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属于给个名誉更可劲地用你,奖金是一分不多的。我总是懒得写什么评论,挂了主笔帽子几个月,一篇都没写过,看来这次逃不过去了。这头一开,以后又要多堆活。
我起来开了电脑,打算查查整个事件现在各方报道的进度。趁系统启动的时候,我给何夕去了个电话。她听上去已经好了,正工作中,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我能想像她一边夹着手机讲电话,一边拿解剖刀剖尸体的情形。恢复就好,至于那个秘密,还是找一个比现在更合适的场合沟通吧。
等到上网查了一遍关于钓鱼案的重要新闻,我不由得苦笑。昨天早晨,上百名被钓鱼执法的车主聚集在浦东城管执法队大门口,要求退回罚款,许多媒体都作了大幅报道。这就是最新的后续新闻了,从新闻本身看,已经算是深度报道,要是没有新的大事件,这新闻的生命就到头了。现在再想起来去跟进报道,汤都怕喝不着,只剩下脚料了。
但有什么办法,就是这个新闻环境,螺丝壳里做道场吧。这个追罚款的新闻本地媒体还都没有报道,我出门往浦东去,打算瞧瞧还能挖出什么边角料来。
已经起了秋风,比往年这时节多了几分寒意。我在路上周转花了一个多小时,午饭是路边买的热狗,一口口吞落肚里,心里却空落落的越来越虚,很不踏实。
书橱里玻璃罐内的太岁总在眼前晃来晃去。对何夕身体的担忧,让我连带着回想起了范氏病毒危机的那些日日夜夜,想起了“等待亡者归来”。是我神经过敏吧,这些年再没有“亡者”的消息,也许早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里腐烂了。
但念头一起,再压下去就不那么容易。拐过这个街角就能看见城管执法队的大门了,眼前是家肯德基,我有点后悔先吃了热狗,但还是推门进去要了杯咖啡。浅啜一口,我摸出手机,拨给郭栋。
2005年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多了个部门,叫特事处。我后来知道,这是个相对独立的机构,直属公安部特事局。所谓特事,就是很特别的事,特别到常人无法理解,或者不方便让常人理解的事。这个世界有太多游离于现有科学体系之外的东西,一旦他们干扰甚至损害了民众的正常生活,特事局就会介入。某种程度上,特事局和更低调的X机构相似,只是一个方向在维护社会秩序,一个方向在科学探索。我怀疑特事局本就是从不知何时成立的X机构里剥离出来的。
不论是X机构还是特事局,都是站在当下科学体系的最前端,面对未知的世界。往往这种时候,大胆的想像会比固有的科学认识更有用。所以这些年来,我和这两个部门都打过多次交道。上海的特事处成立没多久就碰到太岁事件,经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