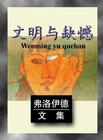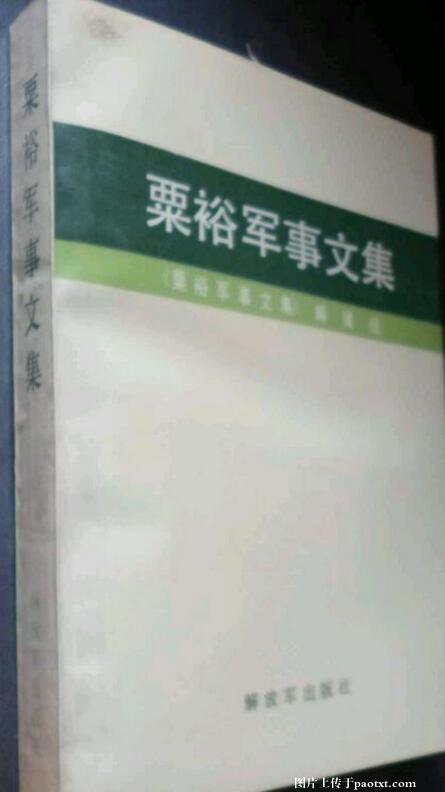石康文集-第6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什么东西至今还在?〃
〃就是我们还是犹太人的时候在燔祭上用的石块。那些石块还在这里,在这个岛上。现在它们还在这里。〃
〃我们能看看吗?〃我问。我感到一阵激动的颤栗。如果梅米尔·菲塞哈刚才说的话是真的,那么,他就提供了一个物证,这个真正的物证证实了他讲的那个故事,那故事虽然离奇,却极为可信。
〃你们可以去看看。〃老僧人回答说。他站起身来,〃请跟我来,我带你们去看。〃
洒血
老僧人带着我们走上了小岛最高处附近峭壁上的一块高地上,峭壁下面就是塔纳湖。这里有个隆起的底座,是一块天然的独体岩石。他让我们看3根聚在一起的短石柱。其中最高的一根大约有一米半的样子,是根方柱,顶部有个碗形的凹陷。其余两根是圆柱,都大约一米高,粗细如同人的大腿。它们的顶部也各有一个凹陷,深约10厘米。
这些石柱上长满了厚厚的绿苔,尽管如此,我还是能看出:它们都是独体石柱;它们各自独立;它们是从同一块灰色花岗岩上凿出来的;它们显得很古老。我问理查德有何见解。
他回答说:〃当然,我不是考古学家。不过我还是要说,从它们的做工和风格上看,尤其是那根方柱……我认为它们的年代如果不是更早,至少也属于阿克苏姆时期。〃
我问梅米尔·菲塞哈,石柱上的碗形凹陷是做什么用的。
他的回答是:〃用来盛血。燔祭之后,把一些血洒在石头上,把另一些血洒在遮约柜的帐篷上。剩下的血就装在这些凹陷里。〃
〃你能给我演示一下怎么洒血吗?〃
老僧人叫来另一个僧人,低声吩咐了几句。那僧人快步走开了,几分钟后回来时,他手里拿着一只碗。那碗的碗口很大,但碗却很浅,由于年代久远,它已经锈蚀,失去了光泽,我甚至猜不出它是用什么金属做的。老僧告诉我们,这就是〃gcmer〃,燔祭上的血先要被收集在它里面。
我问温德姆说:〃'gcmer'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耸了耸肩膀:〃我不知道。它既不是阿姆哈拉语里的字,也不是提格雷语里的字。听上去,它不属于任何埃塞俄比亚语言。〃
我看着理查德,向他请教,但他也承认自己没听说过这个字。
梅米尔·菲塞哈只说那碗叫〃gcmer〃,并且一直被叫作〃gcmer〃,他只知道这些。接着,他站到石柱旁边,左手拿碗,右手食指在碗里蘸了蘸,又猛地把右手甩过头顶,然后一上一下地挥动着。他说:〃就这样洒血,把血洒在石头上,洒在遮约柜的帐篷上。然后,像我告诉你们的那样,照这个样子把剩下的血倒进石柱顶上的小坑里。〃说着,他用碗斜对着石柱顶部那些碗状的凹陷。
我问老僧人,放有约柜的帐篷究竟是在哪个岛上?他却只是回答说:〃离这里不远……就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地方。〃
于是,我便设法澄清我们方才的讨论:〃你告诉我说,约柜是在1600年以前从塔纳·奇克斯岛被送往阿克苏姆城的,对吗?〃
温德姆翻译了我这个问题。梅米尔·菲塞哈肯定地点了点头。
〃很好,〃我继续说,〃现在我想知道,约柜又被送回来过吗?在任何时间,出于任何理由,约柜又被送回这个岛上过吗?〃
〃没有,它被送到了阿克苏姆,一直被放在阿克苏姆。〃
〃据你所知,约柜今天还在阿克苏姆吗?〃
〃是的。〃
看来我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信息了,不过我的收获已经使我十分满足了,尤其是这些信息不是用钱买来的。为了表示感激,我拿出一张100比尔的钞票,作为对寺院开销的捐献。然后,经过梅米尔·菲塞哈的允许,我给这些燔祭石柱拍摄了各种角度的照片。
我们回到巴哈达尔镇的时候,已经快到晚上8点了。我们的塔纳湖之行用了14个多小时,而〃MV达拉克号〃汽艇的总租金则达到了750美元。
无论以哪种标准衡量,这都是代价高昂的一天。不过,我已经不再抱怨自己的开销了。我在达伽·斯台方诺岛上的疑问曾使我感到困惑,而这个疑问却已经被塔纳·奇克斯岛驱散了。现在,我觉得自己可以怀着一种被刷新的责任感和乐观态度,去继续我的考察了。
回到亚的斯亚贝巴以后,我这种积极的心境又得到了加强。我计划在11月23日星期四去济瓦伊湖考察。此前我还有一些时间,去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核对一下《旧约》中有关犹太教使用燔祭石的经文。
我发现,与塔纳·奇克斯岛上的石柱近似的石柱,同犹太教的一些最早阶段有关,它们来自西奈和巴勒斯坦。那些石柱被称为〃masseboth〃,被竖立在高地上作为祭坛,用于拜祭和燔祭仪式。
我翻阅了《圣经》,看是否能找到对《旧约》时代正式燔祭具体细节的说明。我真的找到了这样的细节。我反复阅读有关经文,认识到了一点:梅米尔·菲塞哈在岛上向我描述的那种洒血仪式,的确是一种真正的、非常古老的仪式。在代代相传下来的传统记忆中,这种仪式无疑是被搞乱了,被混淆了。不过,他谈到洒血仪式的时候,却惊人地贴近历史事实。
例如,在《旧约·利未记》第4章,我读到了这样一句经文:〃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慢子弹血七次〃(第6节)。同样,在第5章也说到:〃也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流在坛的脚那里。〃(第9节)
然而,直到我阅读《米什纳书》(Mishnah),才真正理解了梅米尔·菲塞哈的叙述是何等真实。《米什纳书》记录汇编了早期的口头犹太律法。在《米什纳书》的第Th部分的一篇叫作〃Y。ma〃的短文里,我找到了一段详细的描述,其中讲到:大祭司在所罗门圣殿里进行燔祭仪式,仪式在遮蔽约柜的一道帐慢前举行,那道帐慢是为了防止会众偷窥约柜。
那段描述说,祭牲(无论是绵羊、山羊还是小公牛)的血被收集到一个盆里,再指定一个人〃去搅动……以防凝固〃。然后,从圣所里走出一位祭司,〃从他那里接过正被搅动的血,再回到圣所里,站到原来站的地方,向上弹血一次,向下弹血七次。〃
这位祭司弹血时,究竟站在什么地方呢?《米什纳书》上说:他把血弹到了〃约柜对面的帐慢外面,向上一次,向下七次,其意图似乎并非上下弹血,而像在挥鞭……然后,他又向祭坛的洁净表面上弹血七次,再将余血倒出〃。
在我看来,梅米尔·菲塞哈很可能读过《米什纳书》。作为基督徒,他本来没有理由这样做,何况在那个偏远的岛上,他也不可能读到这部书;此外,他也不懂翻译《米什纳书》的那种语言。尽管如此,他向我演示洒血仪式时,他双手的动作却的确很像在挥动鞭子。他还很有把握地说,燔祭时祭牲的血不仅要洒在祭坛的石头上,而且要洒在〃遮约柜的帐篷上〃。
这些联系实在太密切了,根本无法忽略。我确实感到,在遥远过去当中的某个时刻,犹太人曾把一件具有重大宗教意义的东西带到了塔纳·奇克斯岛上。尽管那件东西到达该岛的推测日期与历史年代相左,但还是完全有理由假定:那件东西很可能就是约柜——梅米尔·菲塞哈对此显然深信不疑。
第十章 迷宫幽魂
在塔纳·奇克斯岛上,我和梅米尔·菲塞哈讨论时,这位老僧人谈到他那个主要观点之前曾说过一番话,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现在,我正在埃塞俄比亚研究所的图书馆,打算对这番话的含义做进一步的考察。
这番话谈到了约柜进入埃塞俄比亚的路线。这位僧人说,约柜被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偷出以后,先是被带到了埃及,后来又沿着尼罗河以及特克泽河被带到了塔纳湖。
我在此前几个月虽然已经做过一些研究,但我现在还是明白了一点: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门涅利克一行行进路线的问题。因此,我想看看《国王的光荣》里是如何谈到这个问题的。我还想弄清书中是否存在和老僧人的那个说法相矛盾的地方,那个说法就是:约柜先是在塔纳·奇克斯岛上放了800年,然后才被送到阿克苏姆城。
在这部伟大的史诗里,我所找到的惟一有关信息在第84章。那一章里说,门涅利克一行进入埃塞俄比亚以后,把约柜带到了一个名叫的〃德博拉·玛克姐〃的地方。奇怪的是,书中根本没有提到阿克苏姆。无论〃德博拉·玛克姐〃在什么地方,它都是约柜在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个安放地,这一点非常清楚,毫不含糊。它一下子就解决了1983年以来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史实矛盾,那就是:门涅利克完成回埃塞俄比亚之旅以后大约800年,阿克苏姆城才建成。
我以前的几个消息来源曾告诉我,阿克苏姆是门涅利克此行的最后目的地,而约柜从一开始就被放在了阿克苏姆——这种说法当然不符合历史。可是,我现在却看到《国王的光荣》里并没有这个说法,而只是说,门涅利克一行把约柜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德博拉·玛克姐〃。
我知道,〃德博拉〃(Debra)这个词的意思是〃山〃,而〃玛克姐〃(Makeda)则是埃塞俄比亚人的传说中示巴女王的名字。因此,〃德博拉·玛克姐〃的意思就是〃玛克姐山〃,即〃示巴女王山〃。
在《国王的光荣》的简要描述里,我找不到任何暗示说这座〃示巴女王山〃其实就是塔纳·奇克斯岛。不过,按照同样的思路,我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它不可能就是这个岛。
为寻找更多线索,我参阅了一部权威性的塔纳湖地理考察志,那次考察是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我从中了解到,〃奇克斯〃这个名字是在比较晚近的时候才赋予这个岛的(为的是纪念一位基督教圣徒)。考察志上说:〃埃塞俄比亚皈依基督教以前,塔纳·奇克斯岛叫德博拉·瑟海尔岛。〃我立刻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瑟海尔〃(Sehel)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为了弄清它的含义,我请教了几位当时正在图书馆里看书的学者。他们告诉我,〃瑟海尔〃是个杰泽文单词,来自动词〃宽恕〃。
我问:〃'Debra Sehel'这个全称的正确翻译应当是'宽恕之山',我的理解对吗?〃
〃对,〃他们回答道,〃完全正确。〃
这实在是很有意思。我记得很清楚,在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的《帕西法尔》中,圣杯城堡(以及圣杯圣殿)的位置就在〃Munsalvaesche〃(拯救之山——译者注)。对这个字的确切解释曾有过一番争论,不过,不止一位沃尔夫拉姆研究专家都认为,这个字的背后就是〃《圣经》里说的Mons Salvationis,即救赎之山〃。
毫无疑问,〃宽恕〃和〃救赎〃在意义上是相连的,因为从宗教意义上说,要获得〃拯救〃,必先要得到〃宽恕〃。何况,《旧约·诗篇》第130篇里还有这样的话:〃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思。〃(第3节和第7节)
〃救恩〃(redemption)当然是〃救赎〃(salvation)的近义字。因此,我便不禁想弄清一点:沃尔夫拉姆笔下的〃救赎之山〃,是否可能以某种方式与埃塞俄比亚的〃宽恕之山〃有关——而它现在的名字就是〃塔纳·奇克斯〃。
我完全明白,这种推测只能是尝试性的,而从〃Debra Sehel〃到〃Munsalvaesche〃,其实还是个大胆的飞跃。尽管如此,多次研读《帕西法尔》以后,我还是几乎无法忘记其中的一个情节:神秘的圣杯圣殿(〃光滑圆浑,像是车床加工出来的一样〃)坐落在一个湖上,并且很可能是在湖中的一个岛上。
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和法拉沙人的祭祀场所,传统上都是圆形的,这似乎也并非毫无关联。圣殿骑士教建造的绝大多数教堂(包括一些至今犹存的教堂,例如伦敦舰队街的那座12世纪圣殿教堂),都是圆形的。因此,我感到这一切之间都存在着关联,完全忽视这种关联是不明智的(同样,如果过分强调这种关联,也是不明智的)。
同时,我还要考虑另外一个比较确凿的联系,即〃德博拉·瑟海尔〃和〃德博拉·玛克姐〃之间的联系。塔纳·奇克斯(岛)以前的那个名字已经表明,埃塞俄比亚的岛屿名都有〃德博拉〃(Debra)这个前缀(意思是〃山〃)。塔纳·奇克斯岛仿佛就是一座从湖面上高耸起来的山峰,我第一眼看到它时,它也的确酷似一座山。这当然不能证明,《国王的光荣》说约柜被带到示巴女王山,指的就一定是'德博拉·瑟海尔〃。但我还是认为,它至少认为这个岛有可能成为约柜的安放地。
证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便继续考虑门涅利克一行的行进路线问题。我以前一直假定他们是乘船而行——即从埃宗格倍尔的所罗门港(即现在阿拉伯湾的埃拉特港),沿红海到达埃塞俄比亚沿岸。现在,我研读了图书馆员为我提供的《国王的光荣》,发现我以前的假设完全错了。门涅利克从耶路撒冷开始的长途旅行,始终有一个大篷车队,并且完全是走陆路。
不过,他们的陆路之旅到底是怎么走的呢?
描述他们这次艰辛跋涉时,《国王的光荣》使用了讲述想象传说的方式,讲得如梦似幻,充满奇迹,超脱现实,其中很难找到可以辨识的地名和地理特征。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提到了一些重要的具体细节。
离开耶路撒冷以后,这些旅人先到了加沙(在以色列的地中海沿岸,那里至今还有一座同名的城市)。从加沙开始,他们可能沿着著名的传统商旅之路,穿过西奈半岛北缘,进入埃及,不久便来到了一条大河前面。〃我们下车吧,〃他们在此处说道,〃因为我们已经见到了埃塞俄比亚的河。眼前就是特克泽河,它从埃塞俄比亚流出,浇灌着埃及的河谷。〃
从这段文字看,门涅利克一行说这些话时显然还在〃埃及的河谷〃,并且很可能就在现代开罗城以南不远的地方。因此,他们下车的那条河只能是尼罗河。但令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