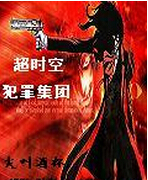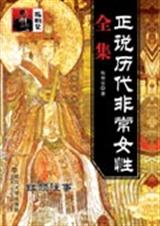季羡林文集-第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人写出,原因是少有人能同时掌握汉文古籍、佛经和梵文。所以鲁迅先生也只能说“尝闻”而已。
这些文章究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入“中印文化关系”和“比较文学”两大类研究之中。这也是季羡林回国后,由于资料匮乏,暂时放弃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而顺时应势,寻到的新的出路。不意有了这个开头,后来“中印文化关系”和“比较文学”的研究,竟成了他毕生从事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此外,这些文章的研究方法,均属于“考据”一类。以比较文学来说,季羡林采用的是所谓“影响研究”方法,而非“平行研究”方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季羡林对比较文学的看法。季羡林后来在2O世纪8O年代曾倡导比较文学研究,影响颇大。他倡导的也是“影响研究”,而非“平行研究”方法。“影响研究”要求论证的每一步都要拿出证据来,不能凭空想象,随意附会。这种研究方法正是他的老师西克教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也即是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季羡林受其影响,从以上几篇论文中已可看出。后来,这种治学方法,贯穿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之中。
《列子与佛典》、《浮屠与佛》和《论梵文td的音译》,是季羡林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的问世,使中国学坛始知有季羡林其人。
三篇论文既出,季羡林名声鹊起,学坛士林对这位从德国归来的年轻博士刮目相看。
*第五章新时代的幸运儿
一解放,东语系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员人数增加了十倍,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百多倍,从北大最小的系忽然变成了北大最大的系。这是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喜迎解放
1949年1月31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一天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当天新华社发出的由胡乔木撰写,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北平解放》新闻稿写道:
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
……
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进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二十三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打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切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
事实确如新华社的新闻稿所说。1月31日这一天,虽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天气奇寒,但是丝毫也没有影响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的高涨热情。他们冒着大风,挥舞旗帜,敲锣打鼓,拥到北平的大街上,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军入城。
季羡林同北平市民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一个人从翠花胡同住处走到不远的东四牌楼,站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迎接这支胜利之师,观看这历史性的场面。
当天下午,他到西城去看朋友,走到什刹海桥上,正巧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这位年轻的战士,背着背包,全副武装,军帽下一双浓眉,两只眼睛炯炯发光,一身厚墩墩的黄色军衣,已经不新了,但洗得干干净净。季羡林看见这位战士的样子,“心里陡然觉得这位士兵特别可爱,觉得他那一身黄色的棉军衣特别可爱。它仿佛象征着勇敢、纪律、忠诚、淳朴;它仿佛象征着解放、安全、稳定。……只要他在这里一站,整个北京城,整个新中国就可以稳如泰山。”(《黄色军衣》)季羡林左思右想,一时百感交集,很想走上去,用手摸一摸那一身黄色的军衣。当然,他没有真正地走上前去摸,而是仍然走自己的路。但总忍不住回头看了几眼,一直到眼中只留下一个隐隐约约的黄色的影子,这个影子从此便永远镌刻在他的心头。
季羡林和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来临。但是,他也有一段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写道:
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但是,我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我不了解。至于我自己,我当时才四十来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事,都觉得异常别扭,他可知矣。
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也仿佛年轻了十岁,简直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1948年12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时,由于行色匆匆,他来不及同北大的同事们告别,只留下一张便函给汤用彤、郑天挺二位教授:“今日下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难备地走了。一切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未几,国民党政府派人送两张机票给汤先生,胡适也从南京来电促汤先生南下。虽然汤先生与胡适交谊甚笃,但由于他对北大这片学术圣地的深爱和依恋,他拒绝了胡适的邀请,毅然选择了留下。不过,胡适拜托他“维持”北大一事,他倒是尽力做到了。
中国革命胜利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留了下来。北大的著名教授绝大多数也留了下来。有的人明明可以走,甚至南京政府的机票都送到家里,也没有走,而且还有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回来报效祖国。这同俄国十月革命时,大量知识分子出国外流的情况截然不同。对此,中共领导人是很清楚的。
胡适南下后,北大群龙无首,一时成瘫痪状态。教授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校务委员会,主持学校各项事宜。通过选举,汤用彤先生被推选为校务委员会主席。汤先生临危受命,行使校长之职,领导北大度过了新旧更替的过渡时期。
解放军入城以后,2月28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钱俊瑞等十人到校,与学校行政负责人及教授、讲师、助教、学生、工警代表等在孑民纪念堂开座谈会,商谈接管及建设新民主主义北京大学诸问题。下午2时,欢迎接管大会在民主广场举行。二千余名师生员工到会。汤用彤教授致词,表示欢迎接管。军管会文管会主任钱俊瑞宣布正式接管北大,并讲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同时宣布: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立即解散,活动立即停止;训导制取消,党义之类反动课程取消;学校行政事宜暂由汤用彤教授负责。大会后,文管会代表和北大教职员工一起举行游行庆祝。游行队伍先绕场一周,然后出西校门经景山东街、景山东大街、景山东前街、沙滩、操场大院,复入西校门,达民主广场。4时30分,在“庆祝北大新生”、“北大新生万岁”的口号声中散会。
3月5日中共北京大学总支部召开干部会宣布总支负责人:书记林乃燊、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殷汝棠、副书记叶向忠、宣传部长黄仕琦、校政党组书记谭元堃、团党组书记汪家镠(以上为总支委员)。
5月4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汤用彤、许德珩、钱端升、曾昭伦、袁翰青、向达、闻家驷、费青、樊弘、铙毓泰、马大猷、俞大绂、胡传揆、严镜清、金涛、扬振声、郑天挺、俞平伯、郑昕等十九位教授和两位讲师、助教代表俞铭传、谭元堃,两位学生代表许世华、王学珍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汤用彤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主席,许德珩、钱端升、曾昭伦、袁翰青、向达、闻家驷及讲助代表俞铭传、学生代表许世华为常务委员。军管会同时宣布:学校行政工作从即日起由新成立的校务委员会领导。北平市军管会还任命曾昭伦为教务长,郑天挺为秘书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铙毓泰为理学院院长,钱端升为法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胡传揆为医学院院长,向达为图书馆馆长。
五天后,即5月9日,文管会宣布:派驻北大的军管代表和联络员,因校务委员会的成立,决定撤销。①
从此时起,北大没有校长,也没有实行后来通行的党委领导,校务委员会遂成为北大最高领导机构。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51年6月马寅初校长到校就职。
这一段时期,在北大被称为“接而不管”的时期。
校务委员会工作十分繁忙,除领导学校日常的教务、行政、后勤工作外,还要筹建教授会、工会等组织;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组织师生员工参加国庆、五一节游行,声援抗美援朝,向志愿军捐献慰劳品、写慰问信等活动。并且经常请来中央领导人、知名人士、战斗英雄到校作报告,对师生员工进行教育。周恩来、陈毅、陆定一、周扬、艾思奇、范文澜等都曾到北大来作过讲演,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在“接而不管”的这段时期,北大师生心情舒畅,干劲十足,朝气蓬勃,每个人都为北大的新生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喜悦,每个人都希望为新北大尽一点自己的力量。整个北大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
───────
①关于军管会接管北大的材料均引自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该书于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语系空前壮大
季羡林在回忆中说:“人民政府一派人来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
一解放,东语系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员人数增加了十倍,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百多倍,从北大最小的系忽然变成了北大最大的系。这是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这个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194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信,令他感到非常吃惊。打开信一看,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当年的胡乔木面容清秀,说一口带苏北口音的官话,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非常斯文的样子。他们是很谈得来的朋友。同时,十八年前在清华学生宿舍里,夜深了,胡乔木坐在他的床边苦口婆心地劝他参加革命,然而被他婉拒了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当年的胡鼎新还不过是个在学生洗脸盆里撒传单的青年革命者,而今的胡乔木则已经是共产党的高官,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心头。然而胡乔木在信中丝毫也没有一点官架子,而是十分客气地征询季羡林的意见。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言的人材。他问季羡林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看完了信激动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当时的革命热潮中,季羡林正为自己一介书生,满腔热血,报国无门而苦恼。这样好的机会从天而降,无论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大好事,岂有拒绝之理?他立即给胡乔木回信,表示完全同意。
在季羡林给胡乔木发出回信后不久,一天,胡乔木亲自来到翠花胡同拜访季羡林。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肚子里有说不完的话。两人在详细商谈了东语系扩大的问题后,胡乔木特意告诉季羡林:“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胡乔木是个细心人,他没有称“毛主席”,而是用了“毛先生”这个词儿,是考虑到季羡林当时可能还不习惯说“毛主席”所以才这样说的。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表现出胡乔木对季羡林的尊重。
就在胡乔木拜访季羡林后不久,这三所大学的师生便合并到北大东语系来了。
据《北京大学记事》载:
“1949年6月,奉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之命,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合并到我校东方语言文学系,同时中央大学边政学系的两位教师调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1951年1月26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学: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送100名青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印地、蒙古、维吾尔、阿拉伯、越南、暹罗、缅甸、日本、朝鲜及西南少数民族语文,以培养少数民族及东方语文方面的革命工作干部,学习期限4年,学习期间按学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由中央统一分配。这批学生预计今年2月底以前报到,请北大做好学生入学准备工作。”
这批学生按时来到北大,进入东语系学习,东语系得到进一步扩大。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阶段,东语系一跃而成为北大最大的系。仍据《北京大学记事》载:
1952年8月25月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全校教师讨论的情况,编制“新北大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方案如下:
……
十、东方语言学系
专业:
1、蒙古语(教师2,学生3)
2、朝鲜语(教师4,学生31)
3、日本语(教师4,学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