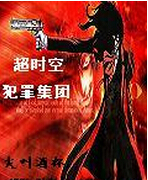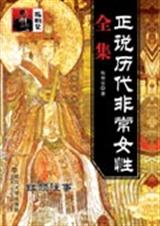季羡林文集-第5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十、东方语言学系
专业:
1、蒙古语(教师2,学生3)
2、朝鲜语(教师4,学生31)
3、日本语(教师4,学生45)
5、暹罗语(教师4,学生39)
6、印尼语(教师8,学生67)
7、缅甸语(教师3,学生28)
8、印地语(教师6,学生45)
9、阿拉伯语(教师5,学生27)
总计:教师42人,旧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干部12O人。
这时东语系的师生总数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第二位是西方语言文学系502人,第三位是物理学系435人。
东语系不但成为北大最大的系,而且是当时全国惟一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过去只有几个人,门可罗雀的东语系,一下子变得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季羡林的“政务”顿时大大地繁忙起来。他要处理系里日常的教学工作,参加各种会议,接待内外宾客,安排全系教师和学生的食住问题,甚至新生入学时他都要去前门车站亲自迎接。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还感到时间不够。这时,他连坐在红楼前长板凳上吃碗豆腐脑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来到学校,在校门口卖烤白薯的摊上买一块烤白薯,边走边吃,便是一顿早餐。中午有时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有时干脆事先买两个烧饼放在办公室,中午休息时,两个烧饼就一杯热茶,午饭便解决了,然后继续伏案工作。好在这时他的女儿、儿子都已经上了大学,济南老家有婶婶和妻子照顾,他每月按时寄钱回家,日子过得平平安安。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除了东语系的工作外,季羡林还成了一名热心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是筹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即后来的工会)的活跃分子。可是,到了真正组建教职员联合会的时候,却遇到了未曾料到的极大的阻力:北大的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教职员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怎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幸而当时一位高层领导人发了话:“大学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有了“上头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顶。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季羡林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1952年北大由沙滩迁往西郊后,又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他这位“资产阶级的教授”竟然领导北大工会好几年时间,今天看来,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说明季羡林当时的工作是颇得人心的。由于担任北大工会的领导工作,季羡林在北大名声大振,不但全校的教职员熟悉他,就连北大的工人也都认识他。当时季羡林万万不会想到,为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而且成为北大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最好例证。他说:“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此是后话。
1951年,季羡林又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他的工作更加繁忙,参加的会议更多起来。人民代表的任务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在人民与政府间起到桥梁作用。
据《北京大学纪事》载:
“1951年3月9日下午,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内容:北大参加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钱端升、季羡林等传达市人代会的决议,并详细报告了大会对北大所提出的39个提案的处理经过。师生们听到自己的意见被提到大会讨论并有了结果,都感到兴奋、满意。”
由于工作热情太高,担任的职务太多,季羡林陷入了会议的漩涡之中。这使他既兴奋又有点为难。他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说:
我本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
三四十年后,经过各种会议的千锤百炼,季羡林已经从一个害怕开会的生手变成了开会的行家里手。他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教授。
凡是同季羡林一起开过会的人,都会知道他参加会议的几大特点:一是提前十分钟到会场,决不迟到;二是发言不说空话、套话,言简意赅,说完就完,决不拖泥带水;三是语言生动有趣,偶尔说几句诙谐幽默的话,引得哄堂大笑,使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四是他主持的会到点散会,决不拖延时间,让与会者都能准时吃上饭。
从1949年到1951年的两年间,季羡林整日忙忙碌碌,在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和会议的漩涡中度过。在百忙之中,他还抽出时间,和曹葆华一起翻译了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长文在《新建设》上发表。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踊跃捐献支援志愿军。季羡林当时身无余财,便找来一本外文资料,同陈玉龙先生一起翻译,发表后将稿费捐献。这些行动表明了季羡林在解放初期,对马列主义和新政权的积极态度。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但不觉得劳累,反而感到生活很充实,很兴奋,认为自己是真正地在为人民服务。
洒满阳光的日子
1951年中国政府决定派出建国后第一个大型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正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在拟定代表团名单对,他又想起了季羡林。他了解季羡林长期从事印度语言文化研究工作,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北大东语系主任,是这个代表团的理想成员。他立即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季羡林是否愿意参加?季羡林一接到胡乔木来信,立即表示非常愿意参加。季羡林研究印度语言文化多年,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天赐良机,岂有拒绝之理?于是季羡林成了代表团团员,随团出访印、缅两国。这是他建国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他后来曾多次出国访问,到过三十多个国家,也曾几次重访印度、缅甸,但是这第一次的出国访问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兴奋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对他思想震撼最大的一次,使他终生难忘。
季羡林本来是个很怕见官的人,更讨厌摆官架子的人,对官场那一套低级庸俗的东西深恶痛绝。他这脾气,在前一章叙述他归国途中的遭遇时已经提到过。但是,季羡林一生中都避免不了要同官场打交道,他对官也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对策。他说:
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怀念乔木》
事有凑巧,解放后,季羡林年轻时的两位好朋友胡乔木和乔冠华都做了大官,而且官越做越大。这南北两个乔木,都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到后来,一个执掌意识形态大权,一个执掌外交大权,名满天下,权重一时。如果是一个官迷,碰到这种情况,可就是碰上了向上爬的绝好机会,只要多跑两趟,跑出个官来当当,是绝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季羡林不是这样的人,他对“二乔”,不但不趋附,反倒退避三舍,有意回避,以避攀附之嫌。
季羡林同胡乔木本来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胡乔木几次主动征求季羡林的意见,还亲自到季羡林住处拜访,没有半点官架子,这使季羡林觉得他不属于那一类低级趣味的官,两人的联系便比较多起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但多半还是胡乔木主动来看季羡林。1993年,胡乔木去世后,季羡林写了一篇悼文《怀念乔木》,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并且表达了自己对胡乔木的看法,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胡乔木的看法相左,颇引起过一些议论。
不管怎样,季羡林还是认为,这次能够有幸参加代表团出访,与胡乔木的举荐是分不开的。他说:“这次出访,当然要感谢乔木。”
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多是文化界的名人,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丁西林任团长,团员有:郑振铎、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冯友兰、季羡林等。秘书长是刘白羽。明眼人一看名单,就知道这是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的高规格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因为这个团是首次在国外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很重要,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组团工作,亲自审查出国展览的图片。1951年整个夏天团员们都在做准备工作。最费事的是画片展。因为要通过展览,才能让国外了解新中国的变化和成就。于是,到处拍摄、搜集最能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图片。最后汇总在故宫里面的一个大殿里,请周恩来最后批准。季羡林同全体团员一起,过了一个异常紧张但又兴奋愉快的夏天。
1951年9月20日,代表团离开北京飞抵广州。在广州又住了一段时间,将讲稿和文件译成英文,做好最后准备工作。当时广州解放时间不长,国民党的飞机有时还来骚扰,特务活动也时有所闻。团员们出门,都有怀揣手枪的保安人员暗中保护。
来到广州,季羡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抽空到岭南大学陈寅恪先生家中拜谒。陈先生见季羡林来访,心情极好,师生相谈甚欢。陈师母唐筼女士亲自下厨,设家宴招待季羡林。然而令季羡林料想不到的是,这次拜谒恩师,竟然成了永诀。
代表团在广州稍事停留后,即乘车离开广州赴香港,然后由香港乘船到仰光,在缅甸住了三个星期。又乘飞机抵加尔各答。在印度住了六周,几乎遍访了印度全国的各大城市及佛教圣地,一直到亚洲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最后又由原路返回香港,于1月24日回到北京。
代表团从1951年9月2O日离开北京,于次年1月24目返回北京,前后足足有四个月时间。出访时间之长,是后来少有的。
当时中国和印度、缅甸的关系正处于亲密友好的时期,新中国首次代表团的访问,受到印度、缅甸政府和人民极为热情的接待。这次访问给季羡林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印象。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回忆这次访问的经历:
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不能忘记,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上面说的这些良辰美景,奇山异水,宫阙胜地,使季羡林心荡神怡,留恋不舍,念念不忘。这固然使他觉得不虚此行。但是,在访问中,真正使他感到心灵震撼,永志难忘的还是另外的一件事。
那是代表团从缅甸仰光乘飞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机场的一幕:代表团走下飞机,踏上印度的土地,在机场受到两三千人热烈欢迎。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上面飘扬着红色的旗子,响起《东方红》的歌声和“中印友谊万岁!”的口号声。代表团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套上了四五个浓香扑鼻的花环,无数双热情的手伸向每一个团员。代表团被人潮簇拥着走出机场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在不远的地方,在木栅栏以外,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印度人,手里举着旗子一类的东西,拼命地对着他们摇晃,嘴里大声呼喊着不知什么口号。季羡林好奇地走到这群人面前,蓦地一声:“毛泽东万岁!”破空而出,声音洪亮清晰。季羡林闻声,顿时感到浑身震撼,眼泪夺眶而出,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解放前,季羡林在国外呆了十一年,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在国外的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和歧视,季羡林耳闻目睹这样的事太多了。这些事情曾经一次次地刺伤着他的爱国心。今天,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他亲耳听到印度人喊出“毛泽东万岁”的口号,怎能不使他自豪、骄傲,进而对毛泽东、共产党更加崇敬和拥戴呢?
对这次出访的感受,他曾在《寿作人》一文中说:
我们团员几乎每一个人都参加工作,参加劳动,大家兴致很高。我同作人,年纪虽轻,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当时我们看什么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辉灿烂的。我们都怀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既兴奋,又愉快;既骄傲,又闲逸的,飘飘然的感觉,天天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
季羡林这段话道出的心情,其实不只是在出访的四个月里的心情。自打1949年北京解放开始,直到这次出访,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都“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
但是,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