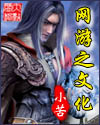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尹有些迫不及待地作了很精彩的演讲,他的样子和蓬松的发型,总让人觉得他更象是诗人而不是一位建委开发办的官员。老尹这个人,激情得很,一腔赤子襟怀,他对于文化中国与文化重庆的未来,是执着颇为看好的乐观态度的,而同时,他也直接提出了文化后殖民时代的忧患。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就是这种后殖民时代的经典写照。
清源作为主讲嘉宾,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与重庆直辖文化建立和发展的两个重要建议:包容和创新。他认为重庆本土的文化很顽固,也不开化。这里我插了一个个人意见,说不是顽固,而是社会对文化的忽略与文化的低关心度(我在想如果大家都能把文化视作为另一种财富或物质力量可能会更快地帮到我们的国人对它予以重视)。
由君辉先生邀来的王先生是重庆文联主席(似乎是这么一个职位),然而却是一位古道侠肠的长者,魁梧的身体,侃侃而谈,其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重庆都市圈文化和三峡文化的概述令人佩服。他似乎在文化的政策之下呆得太久或者是过多地领略了文化的官场力量,因此,当他看到《软实力》和《城市黄页》以及关于书博会的宣传资料时几乎有些不相信。他审视我,他问我:这都是你在做么?别人告诉他是的。于是他就很仔细地看。后来我明白了,他要看看眼前的事实究竟是否是一种真实。我想,这场座谈会以及后来种种的热烈讨论表明了这种现实的真实性。我想起我父亲,对于我的所为也是几乎不能相信的(因为他是过去那场历史中的右派)。我理解这一切,同时,更感受到那种来自于先秦思想者和司马迁时代直至今天中国文化灵魂中独立精神的可贵。而###书记在文代会上所指出的“推动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焕发创造激情,激发原创能力,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传统,积极学习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人类文艺发展史上谱写更加绚丽多彩的篇章”,应当是这个中国时代文化华章的序幕。我相信,历史总会有那么一瞬,产生于时间与空间以及它们所面对的人类中,事实上,这样的瞬间总是那么的多,而同时又是那么的稀少,多是它的客观存在特性,而少,则是它的发生需要将自然宇宙以及人类自身认识的所有能量集于一体,尽管它仅仅只是一瞬,然而足够击发出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一点,可以类同于G点理论,即大爆炸理论。
现在,这个中国文化再一次的G点,它来临了。这种来临,不能不看到它背后更大的一个全球化力量。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应当善于观察并体会这种文化的力量,无论它是处在自然宇空还是人类社会中,我们应以一种尽可能符合客观的态度来观测,这种客观的观测之外需要一些想象力,也需要一些耐心,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对文化这种虚拟能量认知和肯定的信念。就如我都许多场合所表述过的一样:这个文化中国的时代一定会到来。那些曾经听到过这样一句话语的人们,还有许多,他们未必会相信。但它的确是发生了。或许,这样一场小小的座谈,或许将是中国文化的新开端也未可知呢。
一场关于中国文化未完待继的讨论(2)
清源的思想中有很开放也很人文的东西,这些东西我都很喜欢。记得刚与他交往时,我就有这样的印象,后来渐渐相熟了,便颇感默契,于心有戚戚然。叮当是一个腼腆而诚信的朋友,我们才交往过一次,是在创造精英俱乐部的首次论坛上,他是一个执著于儒家文化的人,今天他和他的美国藉太太也都来了,他的观点就是推动中国文化应当从自己的文化积累中去发掘,而这种发掘的财富就是儒家传统。这使我一下想起了由董仲舒开始的中国道统文化,看着叮当那种虔诚和执著的样子,觉得这种中国文化想象力的匮乏之深,已是到了骨头了。十几分钟后,我就开始了对他的PK。这是很有意思的:这场论坛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如同戏剧然而更加真实。我会尊重叮当的见解,然而他或许还没有看到这部《华文漫史》(我很快乐地想他一定会看到的包括他的和他执相同观点的太太),我向可爱的叮当提出了锋利的诘问:假若儒家文化有如此之妙却为什么没能让中国文化的今天更加强大呢?如果是简单拿中国文化历史的不幸作为理由是不能够完全解释这一事实的。
我提出了文化的客观论以及想象力作为文化的创新之源的观点。这一观点看来正在被大家所接受。或者说,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以及学术领域,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总是被主观化或是范式化了,而且还有一个很不幸的大众式结论:中国文化的单边主义。很多时候我们所谈的文化只不过是自己的狭隘理解,这种狭隘放而大之也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道统,然而真实的部份却恰恰在于,中国文化的客观立基点就是世界,也是人类整体,科学来看待的话,谈谈文化的中国性或许会更加准确些,也好利于我们来审视、比较和融合人类文化的其它多元,在今天,这种交集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力,将成为中国新文化时代的元动力。在北京,我想苏彤会是支持这一观点的,而许知远,则更是一个身体立行于这一文化立基点的世界中国评论家(这是我给他取的一个绰号,看得出他爱这个国家甚至世界呢)。
王先生在后来作了一些更精彩的发言。大家在十点钟结束座谈的时候都意犹未尽,于是干脆再滞留下来围成了一大圈。王先生将他在明年的重庆文化艺术节的创意发表了,他建议汪洋书记能够将此办成一场世界最大的艺术盛会,他的创意点就是将重庆的两江四岸做成全球最大的舞台,让全世界都来欣赏这座山水优美的城市以及置入其中的内容。这是一个绝佳的立意,也是想象力作为创新力之元的明证。在我提出重庆将以世界城市的战略定位而切线发展时,老先生赞同了,他甚至认为,重庆更像美国。清源也有此同感,而刘晓科也颇有赞同。后来叮当释然了,他和他的太太,随和而宽容的。女画家很漂亮的,她原来学的是戏曲,她对这个晚上的话题有一些冲动,也有许多的见解。前一排时间我向她建议推出一批重庆的名媛淑女文化艺术家,她很赞同,后来又有些退缩。我当时笑她怯。现在看来,一个更大的文化胆子正在形成。当赵君辉先生提及文化工作者尤其是吴扬文这样的工作者应如何做好中国文化政策的对应工作时,我就给大家讲了一个积极的心得:将政策二字掉转过来,就可以策政了,这也是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一个具体表现:人民群众在积极投身到时代和社会之中,发挥首创精神,积极参政、议政,同时还要策政,推动政府产生更多更好的政策改进,这样,才是一个文化倡明的盛世时代。中国的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了。女画家很高兴地击掌,她补充说:这就好象是政治经济,现在,中国讲市场了,就是经济政治。
子夜时分,这个小小论坛才告结束,而且还是主持人庞涛很不忍心地宣布结束的。下一场的接力棒,由刘晓科先生负责。
我记下来这一场座谈会,是想在《华文漫史》中表达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国文化真正的灵魂和生命,便是它的一切流动和变化,以及它的客观性和真实。今天中国文化要做的,就是促成这样的变化。或许,目前尚不能完全能够支持这一些,然而至少,这种改变的时代已经来到。王先生指出:真正的文化属于人民,也是文化的本质。我赞同。而这一点,与今天国家“一切服务人民”的价值倡导完全一致。当时,大家鼓起了掌。就在这些掌声之间,一个中国文化历史的分水岭来到了。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汉风:汉赋乐府与霍去病的石马虎(1)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写的那本《世界是平的》,现在在国内已经很流行了。我在北京机场的时候,机场书店的售货员告诉我销得最好的书就是这本。弗里德曼在这本40万字的书中最后一章里谈到了一些属于个人的看法(很显然这些都来自于他对于全球化进程的种种观察和思考所得)。他认为,想象力是人类的一种可贵的品质,即便商品经济如何发达,而唯一不能被商品化的便是想象力,今天和未来,这种想象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为文化创意经济的生产力,在北京、上海以及国内一些城市,这种新经济已经被点燃。
墨子的时代,兼爱与非攻,以及还有他对于机械物理和光学的种种好奇和研究,以及当时代的诸子思想等等,都是一种想象力时代的开启。而即便是主张苛严之政的李斯,也在谏逐客令中对自己的才能与国家广纳贤明作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说明,使秦王居然不逐他而且还官复原职。我想假使秦统一中国之后,有李斯再进一言,称令诸子百家之徒可尽言天下,举国之良材,可尽显其多能,也就是让大家说,让大家做,一如汉武帝在求茂材异等诏中所说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接着李斯再讲一讲天下是平的道理,想象力是国家的生产力,举现实的例子,做亲身的示范,让那个雄才大略的赢政听得明白了,如果这样,恐怕不仅不会有焚书坑儒之事的发生,也不会有他自己最后被腰斩而夷灭九族的事情发生了。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因为想象力的自由伸张,一个文化繁茂而国政清明的时代将很可能更早地出现在东方的历史上,也不致于有200年后董仲舒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的发生。
事实上,想象力之于中国,便是自2200年前秦朝开始,就从中国的正史上消失了,只有一些种子散落到了民间。
想象力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属于梦想,也属于人类与客观世界的那条自然纽带。这条纽带如果强大,那么人类的创造力与科学认知力则获得快速增强,而且还会表现为充满激情和热爱生活,显示出积极的追求,相反,这条纽带如果断裂或者严重畸形,其结果会很糟,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将是愚钝,对客观事物缺乏感应力。很不幸,这一结果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成为了我们的历史。
弗里德曼在他的书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评论:如果一个社会的回忆多于梦想,在这个社会中,会有很多人化费大量的时间向后看。他们不是通过当前的努力而是通过回味过去来获得尊严、肯定和自尊(而不是设想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同时为之奋斗)。当一些国家走上这条路线时,会非常危险。如果美国失掉了他的宽容也朝向了这个方向,那就将是一场灾难。
这一段话,可以视作一个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的一句忠告。然而这样的逻辑和思想,即使是在2000年前,也并不是不可能产生的。“想象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把这个未来设定为国家的理想和目标甚至是人类的目标,并不是不可能的。秦朝统一了六国,平定了天下,这个理想的未来就应当出现啊?看来,秦并不是唯一的那个抑制想象力的人,看看庄子这个想象大师的际遇,我们会发现,或许整个农耕发端的中国各个诸侯,都不怎么喜好想象力,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很现实,就跟今天许多的中国企业家一样,这种风格和偏好并无太大的变化,他们几乎惊人一致地认为想象力总是太虚,而现实才是最好,一切都要落地,落地的东西才令人心安。所以,当未来尚没能形成一个落地的现实时,这个未来也就不再令人相信了。
这恐怕是中国式的特有逻辑了。因此,当未来不可捉摸而现实又如此不确定时,回忆便成为了寻找落地之物的最佳方式…因为曾经有那一些东西在过去某个时刻落过地并成为祖先的骄傲,于是我们,这些东方的后裔们,便有了回忆并通过回忆而获得慰藉的优良传统。
这种传统在汉朝的时代,似乎有了一个转变,变得积极而客观,变得拥有抱负而面向未来。至少汉高祖被人提醒了一把,想到了“天下”,而他的后继者文帝则更富有国家的想象力与同情心,在《文帝议佐百姓诏》中,这位皇帝率先发挥出想象力而反复设问,将一个勤政而恤民的君王态度跃然诏纸之上。这封诏书是针对数年来农耕不收而灾害不断来发布的,意在告民安抚,这些设问的诏文如下:
。。
汉风:汉赋乐府与霍去病的石马虎(2)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至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皇帝尚能如此谦问于天下,天下又如何不作应答呢?这一设问对话的方式,颇有一些海德公园的自由演讲的兴味,那下面的听众,听出了道理,便也就自动去做去了。于是,文景之治后,汉朝的国力大增,直致使汉武帝有了拓疆四方的宏图。从中山小国之谋,到大汉九州天下之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而持续的大一统国家,也首次绽放出一个大国的雄心和这颗雄心之下的文化暗涌。这种大汉文化的酿成,就如酒一般,装进一个橡木大桶,贮存在一个偌大的地窖里,给它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便开始慢慢发酵,开始渐渐香醇了。汉朝对于中国文化,就象这只大桶,而那些酒曲和用于勾兑的陈酿,则是先秦的诸子思想者们。我在上一章里曾说过,假若让中国的文化再与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混和一次,历史也许将是另外一个样子。而现在汉朝的文化,也将是另外的一个样子了。
汉朝文化的兴起,是继战略和秦朝所流行的策、论之后,率先在诗、辞之后所继承并发扬而成的辞赋和乐府诗这样的体裁并获得其特有的文学性表现的。
所有的文化都会因为不同时代的话语系统而显示出文学体态的不同,但总的意涵却是一致的:心为言,言为文,人文而化成。中国文化的长期教育,皆是对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