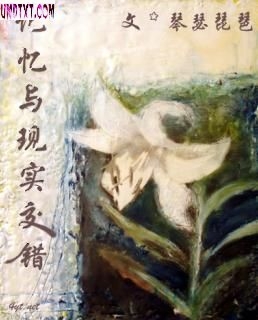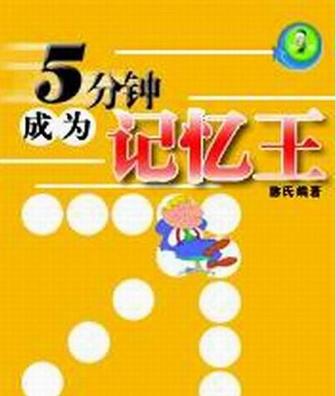香蒲草的记忆-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个时候就这么淘气,如今回想起来,只觉得孩子气十足,认为那样自己就高兴,认为自己那样就开心,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高兴和开心,却惹得别人不高兴不开心,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如今,安祥伯伯的那个院落,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华。鲜花出嫁在下河北村,她丈夫在城里上班,为人精明能干,日子过得还算小康。鲜花她妹妹,人们都叫她二鲜花,和大妹妹秀莲同龄,也嫁在上佐村,她女婿在供销社工作,这几年又承包了个门市部,据说收入还可观。家中最小的是一位男孩儿,他叫永红(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六日出生),和我同辈,很有力气,人又勤劳。村里人都知道,他家坟地里的一块石碑,在他爷爷坟前躺了好多年,是永红把它重新“竖”了起来。去年(指二零零四年)冬天,我和父亲还去看那块石碑,碑文是邢子述老先生写的,石碑上面的字,出自祖父之手。
子女们自有子女们的活法,可就是苦了兰娥大妈一个人,中年丧父,可说不幸,一人又拉扯大五个孩子,实则不易。风里来雨里去,困难没有压倒她,那是她那开朗的性格起了作用。几年前,还有人给她说合一些男人的事情,她怕子女们跟上受气受罪,硬是免了许多口舌和是非。
因为车票一事,偶然想起安祥伯伯的一些往事来,为了他老人家救父亲一命之恩,我不敢有半点轻视他的言语,在此祝他老人家安息,并祝福所有活着的人幸福长寿。
由房子想起同族伯父张宣元
由房子想起同族伯父张宣元
听父母说,我家过去有三间西房,三间南房,还有五间东房。祖父和祖母住在西房,父母住二间靠北的东房,房前有一棵香椿树。西房在我脑海里没有印象,东房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老高老高的坑沿,坑上还贴着花花绿绿的墙纸,记忆好像是在晚上发生的,刚睡在被窝里,就看见一只大老鼠在炕上跑来跑去,我怕它钻进被窝里面,就把被子压得紧紧的。第二天早上,我和父母说了晚上老鼠的事情,他们说,老鼠怕人,它是不会钻进被子里的。我有些相信,可又有些不相信,还是害怕。
拆西房和东房时,我没有记忆。但是,盖正房时的情形,我还有印象。那时,我就是五六岁的样子。听父母说,当时是我大姑父的泥匠,我姨父的木匠,盖房所用的土坯,是妗子和姨姨还有母亲,她们三个女人脱的。
这里又引出一句土话:脱结(取其音)。结,就是盖房用的土坯。脱为动词。“脱结”的工序是这样的:前一天晚上,先将水倒在一堆土里,然后等第二天早晨起来,将水浸泡好的泥倒在一个木头做成的模子里,然后再将泥倒在地上,晾干后即成土坯。这种活儿,我小时候经常做,看似简单,实则费劲。首先用铁锹将浸泡好的泥,翻动好几遍才成。往木头模子里倒时,还要在模子里面洒一些草木灰,防止泥沾在上面。
因为盖我家正房的主要原料,来源于西房,那就得先拆西房,然后才有盖正房的可能。
为什么要拆西房呢?原因大概有二个:一是房子旧了,二是地基低。主要原因应该是第二,这与我村的地形有关,东高西低,一年四季,就怕夏天刮风下雨。一下雨,全村的雨水都流到了村西,院比街低,水自然就流进院,房和院一般高,水又流进家里,老鼠四处乱跑,有时鞋还会像小船那样飘起来。母亲说,一下雨,她和父亲就得赶紧把风箱搬到炕上,风箱怕水,风箱坏了,就不能做饭。那时的墙还是土墙,水一浸,很明显会影响到房子的寿命。一到夏天,祖父和祖母的心就提到嗓子眼那儿,整夜整夜不敢睡觉,怕下雨。就这么提心吊胆,还会遇到老天爷的戏弄,你睡下了,它下起了雨,就叫你防不胜防,有准无备。
居住的东房和西房拆了,正房一时又盖不起来,只好暂时住在邻居的空房子里。记得祖母和三姑还有我,是住在同族祖母有金奶奶家里。有金奶奶有一个儿子,名叫张宣元(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是我的同族伯父。宣元伯伯有个儿子,名叫张贵林(一九六零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生),是我的同族兄长。父母住在哪儿?听他们说,是住在南房里。
由此,我想起一件往事,也是听人说的。意思是同族伯父张宣元把祖上留下的房子给卖了,什么原因?自然有他老人家的理由,可就是那房子卖得有些不合算。一般情况是这样的,过去有钱人家,大多把金银财宝用在修建房屋上,而且房子也比较讲究,有的甚至在房子里做了手脚,就是把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埋在房子某些地方,放在什么地方?只有放得人知道,就连子孙都不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一怕子孙不孝,把钱花了;二是给自己留条后路,晚年有些零花钱。
据说,同族伯父张宣元卖得那些房子里就有这些东西。什么东西?众人不知,就连他老人家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东西,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知道的只是祖上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卖房子时,一定要自己拆了,然后再卖。事情却不是这样。据同族伯父张宣元讲,他也在房顶上走了半天,在房子里也朝上看了半天,可就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把房子卖了。
买主拆房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尘土飞在空中,像是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有一个人印象特别深,好像是下河北村的,一只手没有了,人们都叫他秃手手。其人很瘦,却异常精干,像一只猴子,一会儿窜上房顶,一会儿又站在地上指手划脚。
后来听人说,买主从瓦片底下取出好多银元来,还从大梁上取走“一个金人挑着一担水”。光是这些东西,就可以再买这样的三四个房子。具体情况如何?人们谁也没见,只是猜测,只是传说。
总之,同族伯父张宣元是有苦说不出来,悔不当初啊!后来,他老人家也在一天走了。他老伴名叫刘林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出生),为人言短,一生没有生育。同族兄长张贵林与他女人(她叫张淑贞,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是同族伯父张旭良长女)种着几亩地,生一儿一女,过着消遥自在的日子,还行。
第五章 传
第五章 传
据村里人记忆,明朝时期,或者是清朝时期,村里出了一位名人,他老人家名叫邢养道(取其音),中过进士,当过大官,可说是我村第一大名人。可是我从《忻县志》和《明史》中没有看到有关文字。下来就是邢子述老先生,上过什么大学,和谁是同学?村里人都不十分清楚,只是传说。但是他老人家做过阎锡山的文书,写过一本四册的书,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还有邢善言老先生,村里人都说他老人家当过山西省国民议员,还担任过忻县财政局局长,但是在《忻县志》中找不到相关的文字,也只是传说而已。
——摘文代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枣树坡:记忆中的三位老人
枣树坡:记忆中的三位老人
二零零四年的一天,我回到村里。一进门,见父亲正爬在桌子上,写他那毛笔字。
父亲朝我笑了笑。我知道,这是父亲跟我打招呼。我说我妈呢?
父亲说她出去了,到哪儿我也不知道。
我问起父亲村里过去的一些事情,父亲说他知道的也不多。
然后,他说起枣树坡这个村名。
然后,他又说起始祖名讳兴这位老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枣树坡这个村名,当时在我内心一阵激动。激动之后,又是一阵无限联想。始祖名字我还有些印象,每年过春节前,家里总要摆一种叫“疏”的东西,有时是父亲写,有时是我写,记得第一个写得就是始祖的名讳。村里人称疏,也叫老人,相当于书上说的家谱。
在忻州商校上学期间,也就是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三日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这段时间,我曾买过一张画儿,大小跟年画差不多,画的名字叫“纪念堂”:四周画着青蓝色的松树和柏树,树上面飘着许多祥云,松树柏树旁边是一处祠堂,大门两旁站着一只仙鹤和一只小鹿。仙鹤展翅欲飞的样子,让我联想起逝去的祖父和祖母;小鹿悠闲幸福的姿势,叫我想象着祖父和祖母的子孙。大门两旁木柱上贴着一副对联:
先祖树德功似山重,
父母生育恩如海深。
祠堂大门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的牌位。牌位前面是一张供桌,供桌上有许多祭品。供桌前面是一个香炉,香炉上面飘着的紫烟,给人的感觉就是神秘。画的正上方写着“纪念堂”三个大字,大字下面画的,是过年“摆疏”的那种折子。疏折子原先是空白的,后来父亲把列祖列宗请上去,或许这就是父亲说得那个“茔”。
记得初买回来时,同族祖父张成龙看见了,他老人家也觉得很好,让我第二年给他老人家也买一张,结果是第二年就不见有卖这样的画了。
画中间最上面的一个红框子里,写得就是始祖的名讳,下面自然是他老人家的子孙们。每年过春节时,父亲就把它打扫干净,然后挂在墙上,前面摆上祭品,点上蜡烛,敬上三根香,然后磕头祭拜。
父亲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神态是毕恭毕敬的。我听父亲说话的时候,也是毕恭毕敬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让我分心,让我想起其它事情。
父亲说的枣树坡,也就是村里人现在所指的南窑头。(南窑头)以前是一个村名,后来演变成自然村,现在无人居住,只是一个名称,在我村南面,也在火车道南面。我小时候,记得那儿还住着三二户人家,有五六口人,其中有一个光棍汉,外号叫三迷糊,还是我叫伯伯的一位本家,排行老三,名讳张福海(二十一世)。他老人家的右胳膊不知怎么没了,听人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三迷糊爱睡觉,在哪儿都能梦见周公。因此,人们给他取了这个外号。
有一次,他竟然躺在铁路上睡着了,右胳膊就放在铁轨上,在他做梦的时候,一列火车过来,也就把他那条胳膊给了周公。这是他老人家在太原一段不平凡的经历,那时他可能就是十几岁的样子。幸亏他的头没放在铁轨上,否则后果不可想象,留下一条命,真是福如东海。他吃饭的时候,总是蹲在墙根底,把碗儿往膝盖上一放,左手拿一双筷子,还顺手。我总担心那个碗儿会掉下来,却总不见掉在地上。后来他走了,我没有印象。但是我还能回想他老人家的模样,尤其是他吃饭的那个姿势。
村里人有个习惯,就是吃饭的时候,人人都端着饭碗往大街上跑,就是数九寒天的时候,人们也要端着碗儿,走东家窜西家,好像在自己家里吃饭不香似的。如今也有这种现象,但不是很多。
有的地方,给这种习俗起了一个名称:坐街。
在南窑头还住过一位老人,人们都叫他韩师傅,外地口音。听父亲说,韩师傅是个手艺人,会张箩子,因此人们叫他韩师傅,其实他老人家的名字叫韩富贵(取其音)。韩师傅还有一位老伴,村里人不知道其姓名,只是称呼“韩师傅老婆婆”。老俩口养着几只羊,白天上山放牧,晚上回家吃饭睡觉,不怎么进村,也不怎么和村民们来往,俩位老人像神仙又像隐士,日子过得平平稳稳。
据同族兄长张全根记忆,韩师傅还会打卦算命,并相当灵验。理由是韩师傅曾给异族兄长邢明旺看过面相,说此人长大必定有福,不愁衣食住行,还有节余。事实也正如他老人家所言。而另外一位异族兄长则不尽人意,生活艰难,经常东借西挪,光景过成日月,也正应了韩师傅说得那句话:你能跟人家比?
韩师傅老家是哪儿?他为何来到这里?等等问题,在人们眼里都是谜。好像白石村还有他一位闺女,人们不怎么见他们父女来往,更给人们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后来,这位老人在一天黑夜静悄悄地走了,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儿。
印象中,南窑头还有一位老人,他老人家名叫安大山,好像是从南沟村(位于五峰山下,在我村东南方向,距离好像是七八华里)迁移出来的,他老人家有一儿一女,男的叫安根深(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出生),担任过村里的支部书记,是一名老党员,模样跟小品演员赵本山极其相似。女的叫安金娥(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出生),听村里人说,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叶茂。把兄妹俩人的名字连起来,就是根深叶茂,取意为儿孙满堂,兴旺发达。
记得他老人家那双手有些发抖。人们说,那是他老婆跟人走了之后气成的毛病。他媳妇名叫邢秀芳,有个小名叫秀子,生下两个孩子后,嫌自己老汉没本事,跟上南沟村一位男人去了大同,人们都说这位男人叫涛子,这可能是小名。自己老婆让人拐走了,又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那个年代,你叫一个大男人怎么活呀?他老人家越想越气,越气越想,最后心里那气儿,就跑到他手上了。心情一激动,两只手就发抖。尤其是他卷旱烟的时候,手越发抖动得厉害,卷烟纸里的烟末儿,也让他抖落了一地,别人看见了,只好给他帮忙。
他老人家有个孙子叫安保旺(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出生),和我同岁,娶了一个好媳妇,生下二个听说的儿子,日子虽说过得有些紧张,但是全家幸福安康,算是对他爷爷的一种安慰。 。 想看书来
枣树坡:我梦中的天堂
枣树坡:我梦中的天堂
可以想象到,六百年前枣树坡这儿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和睦,以及和睦产生出来的那种祥和。土窑洞前那片枣树林,给孩子们带来的欢笑,给人们带来的甜美,以及由欢笑和甜美带来的幸福,有谁能想象到啊!
在枣树坡南面,还有一个大院,里面还有几棵杏树,树干有一人粗,树的年龄早已成为历史。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品尝到历史留给后代的山杏,可见历史是那么遥远,我们不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