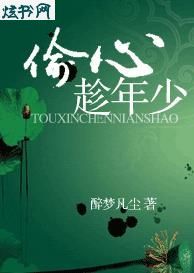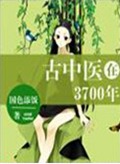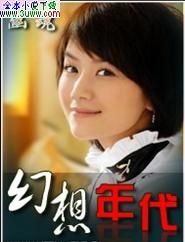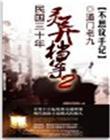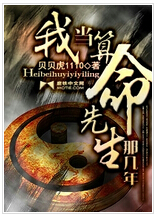我这九十年-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晓……”、“锄禾日当午……”、“床前明月光……”,就四句,我都是一下儿就背下来了。背诵给父亲听,他很高兴,便又教我背《木兰辞》。那可不同于四言诗,我几次都没背下来,父亲就骂我狗东西不用心,还罚我跪着背。我哭说,《木兰辞》太长了,我背不下来。父亲耐下心来讲,《木兰辞》是一首南北朝时候的好诗,在文学史上很有名,小孩子都必须会背等等。我听父亲的话,认认真真背了下来,背得烂熟。说来奇怪,后来我再没背过它,但八十多年后,我一张口,还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苦读诗书、改换门庭的清末举人(3)
父亲成了举人以后,亲戚们对我家就另眼看待了。民国后,他更受尊敬,大事小事常被请上。到我出生后,已经没有原来穷困时,父母和姐姐们受到的那种歧视了。我母亲家人多,她那边的亲戚就特别多。我共有五个舅舅、五个舅妈、十个表兄、十个表嫂、九个表姐、九个表姐夫。他们谁都比我大好多。那时我在玩耍年龄,跟我玩儿的小伙伴们,却都管我叫“六姨”、“六姑”。老在一起玩儿的,除了我姐姐的孩子们,还有我三表姐的女儿金枝,她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我四表兄的女儿仙枝,比我大一点儿,也跟我一块儿玩儿。仙枝大名叫张觉民,后来出去念书了。她在北京上学时,跟我二姐的孩子济世相好,表兄妹就结婚了。仙枝那时挺妇女解放的,我记得她给我父母亲的信里说:“叙(济世字耀叙)爱我,我爱叙,于是乎我们俩结婚了。”仙枝的小弟弟,身材不高,我叫他小黑子,“*”后跟我有联系,还曾打发他的女儿张蓉芳来家里看我。他这个女儿长得高,是我们国家特别优秀的排球运动员。
我几个舅舅都念过书,学过些旧学。大舅担任一家之长,总是威严,全家人都怕他。他很高寿。二舅却在中年时就病死了。二舅好像很有名望,去世的时候,非常排场,一跪一大片人,从南禅院庙里请来好多和尚,念了七天经。我们每天晚上都去那儿跪着,披麻戴孝。我母亲的小弟弟——我五舅,在1926年土匪攻陷新蔡县城后,被土匪绑走撕票了。五舅是个儒医,并不有钱,但很有学问,喜欢侃侃而谈。我父亲爱跟他聊。我们家人有病,都找他看,与他感情很好。母亲失去这个小弟弟,非常悲痛。父亲在那年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此次匪灾,惟五弟受祸独巨,人亡家破,惨不忍言,路人闻之,亦当陨涕,况至亲乎!五弟素好谈论,与吾家踪迹最亲,岂意夏间一别,竟成隔世,思之痛极!”
我那十个表兄,只有四表兄一人在外面工作,其他九个都一直在家。他们里面,最数六表兄长得魁伟,人也洋气。他娶的六表嫂也洋气,那时候就穿裙子。六表兄写一手好字。我家影壁墙上的字,都是母亲请六表兄写的。我的十表兄最小,是我二舅的儿子,白白净净,人也老实。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他一灰心,自杀了。1981年,我和丈夫王一达回新蔡时,还看到过十表嫂,她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孤零零的。那次回去,我的七表兄还活着,但走不动了。我们去看望他,他让家人给做了好多吃的,吃不动了还上菜。1997年我和一达再回新蔡,他们就都不在了。九个表姐、九个表姐夫,我自抗战开始离家后,就都没再见过。我五表兄有个儿子改名谷风,十几岁就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很有才气,是歌剧《茶花女》的第一代中国导演。他的旧体诗词写得很好,我非常喜欢念。可惜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东北农场劳动二十年。“*”后,他常来看我。总之,我小时候,母亲那边的亲戚往来特别多。我念中小学多在开封和北京,寒暑假一回来,柜子里满是表姐、表嫂们给我做的绣花鞋,穿不完。
父亲出身贫苦,家境好起来后,始终保持跟贫苦人家平等,助贫济困。他出门有时乘推车,但在路上遇到地里干活的农民,会立即下车,走过去跟人家打招呼,一点儿不摆举人架子。夏、秋收时,佃户往家里送粮,父亲和母亲就专请厨师,给佃户做肉做菜,炸油疙瘩,摆好几桌。我小时候看见,给父亲送礼的人很多。父亲不要,劝他们拿走,但他们一定要送。父亲就把人家送的东西放到街门外去。现在想来,父亲真不怕得罪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传统家长(1)
我父亲一生只有六个女儿,没一个儿子。他五十来岁时,我出生了,以后就再没有孩子出生。没生儿子,母亲怪自己,觉得对不住父亲,便劝父亲纳妾。过去讲究女人贤惠,三从四德,包括“夫无嗣,劝娶妾”。
母亲给父亲选了一个年轻女人,姓赵,纳进家门。我记得那个女人身材小巧。父母亲谈论她的时候,包括书信里,都称她“赵妾”,但让我叫她“婶”。我的姐姐们不管岁数多大,也得管她叫“婶”。这种尊卑有序的规矩,家里很严格,不能破坏。父亲在西安做事时,母亲也曾给纳过一个妾。那时我小,不记得她姓什么,只记得我也叫她“婶”。
1925年阴历六月一日,父亲在河南全省自治筹备处期间,从开封写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关问母亲病情和我的情况,问及赵妾:“汝痢症复发否?平女仍顽健如恒否?均极系念。赵妾想已移与汝同屋矣。此问家中大小清吉。”父亲信中总叫我“平女”,因为我原名任平坤。赵妾——这个“婶”对我挺好,而且与我母亲相处融洽,母亲病时,她还帮着照顾。
北伐时期,1927年2月11日父亲在给母亲的一封短信里,催盼相聚,也提及赵妾,信的全文是:“梦吉我妻如面。我于十二日来濮阳看望雪亚,住六七日,约一二日内即归开封,径赴武昌。我妻能将家事从速结束,早日前往,极所盼望!雪亚军事上发展甚为顺利,真能为主义奋斗,我此来甚为满意。家中近状如何?极念!赵妾果不愿回,亦只好由他。此问汝好。平女均吉。芝铭手启二月十一日。”信中所提“雪亚”,是那时期的镇嵩军统领刘镇华。
父亲在张轸的第十八师时,1927年12月15日从武汉写的一封信里,问母亲道:“赵妾服从性较前如何?”父亲有齐家原则,要求妻妾分明,妾是要服从于妻的。
可是,赵妾进家很久,也没生出儿子来。不但没生儿子,连个女儿也没生。西安那位妾也是如此。都不生养,从现在医学上看,就应该不是女方的生育能力有问题了。
赵妾在我家时间挺长的。但抗战前父亲在河南通志馆做事期间,她有所不轨,父亲一怒之下,把她休了。为这事,父亲在1932年6月20日给我母亲的信里,表露了愤怒:“另外给赵一个休书,教他赶快离开我家……忽又接到赵氏来信,不知是哪个王八旦替他写的,竟敢称起‘妻’来了!”
父亲是从旧文化里熏陶出来的,作为肩负齐家之任的一家之长,很重视尊卑有序,只有我母亲才可称“妻”,妾是不能称“妻”的。所以,我们家不像现在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太太、二太太”、“大夫人、二夫人”的,不分妻妾。那样就乱了尊卑了。赵妾是妾的时候,父亲称之“赵妾”,休了,不是这家人了,就称“赵氏”、“赵”了——像信里那样。
休了赵妾后,父亲因母亲为此事劳心,当年11月9日写信表示愧歉,又问及赵:“赵氏已搬出西街否?想既有多人说话,必不至再有纠缠了。此事累吾妻着急费心,真教我愧悔万分。”
现在存世的父亲给母亲的几十封信,都是上世纪20年代到抗日战争前写的信,从印有单位名称等的信纸,可以查知年代,有:中州大学用笺、陕西省长公署用笺、河南全省自治筹备处用笺、× 军总司令部用笺、陆军第十师司令部交际处用笺、孙文头像总理遗嘱信纸、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司令部书记处用笺、长沙警备司令部用笺、河南通志馆公用笺,以及宣城生花阁印信纸等。父亲寄信的信封,现存不多,有:长沙警备司令部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司令部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后方留守处,以及一些手写寄信地址的。
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传统家长(2)
父亲多在信封写上寄信地点,从现存信封可见:芝铭由长沙警备司令部缄、芝铭由长沙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司令部缄、芝铭由武昌斗级营庆云旅馆缄、芝铭由武昌紫阳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后方留守处寄、由武昌紫阳桥工程营巷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后方留守处任寄、由长沙第六军十八师师部任缄、由湖南醴陵县任寄、由长沙洪家井任寄、由上海北车站忠兴旅馆任寄、芝铭由开封北仓小学对过三十三号黄寓寄(这是我大姐任馥坤家地址,大姐夫叫黄志烜,父亲有信专嘱此“馥女”地址)等。信封上的收信人,父亲一般都写“任张梦吉收启”,拖人带的信,也写“梦吉贤妻手启”。
从信纸、信封和那些信的内容能看见,那些年,父亲在养家糊口的同时,“为主义奋斗”,为今是学校忙碌,到处奔走,居无定所,思妻想女,深情切切,洒布纸上。我今读来,亦泫然泪下。如:“吾妻近状如何?平女见吾出门,要与同行。不知吾去后又作何状?思之心痛!”“来信谓平女念我,我又何尝不时时念家?”“吾意本年暑假,辞馆回县,否则年终亦必辞去。盖吾夫妇均年近花甲,尚能相处几日……藉以享骨肉团聚之乐,免老年奔波之苦。”“我离家日久,思之成梦。如果县境稍靖,本年四月初定须回里。”“梦吉我妻如面。抵汴之次日,即发去一片,报告平安,计早接到。”“略迟当回县一视,因吾心亦极思家也。”
父亲出门在外,总想接我母亲去同住,如信中有:“吾妻可将家事料理妥叶,略作结束,即托刘表外甥与其妻为吾家分场看门,亦自可靠。来陕后一年半载,略有积蓄,即与吾妻同归,不再在外干事矣。”“你能将家事结束,早日赴鄂,实所至盼。”
1926年新蔡县遭匪灾后,父亲连信询问:“我妻与平女及诸亲友,均是否安全?忧念焦劳、夜不成寐者,已一周矣……家中财物损失,尽可置之度外,所最时时放心不下者,惟吾妻与平女之现状如何而已!”“平女经乱离后,曾受惊恐否?吾妻痢症,近痊可否?均极念!”“匪破城时,烧杀极惨,彼时满城号哭,逃死无所,吾妻与平女必俱惊悸亡魂,思之心痛!平胆素怯,事后俱不至生他病否?汝痢症如何?”
因为姐姐们都已在外,或游学,或婚嫁,只有我年幼在家,且是最小,所以父亲信中问我最多。但他的信里也常讲到“馥女”、“纬女”、“载女”、“叙女”等姐姐们。父亲对晚辈的称呼总是这样,晚辈名字中间的字儿,加上其在家中的身份,如说女儿任纬坤“纬女”、说女婿孙炳文(字浚明)“浚甥”、说外孙孙宁世(孙泱)“宁外孙”、说过继孙子任济世“济孙”等。只是给我的信里唤过我“平坤我儿”。
父亲在开封做事时,把我接在开封上学。母亲也住过去了。那之前父亲在多封信里催促母亲前往开封,如:“梦吉我妻如面。顷发一函,嘱将家事安置妥当,即携平女来省。”“吾妻本月底能早赴省才好。”“现已存中国银行专备吾妻来省费用。”“吾意县中居住,总多危险,不如来省较为安全……可请伯英送至颖州,由彼处搭小火轮至蚌埠,再由蚌埠搭火车到徐州,换陇海车,即至开封。”
三姐家和大姐家曾在开封居住。父亲被聘为河南通志馆协修后,在开封工作,但没买房子,住过三姐家、大姐家,也在万寿街租过一个小旁院。父亲在给母亲一封信中提到:“与馥女、载女等商量,目下正值运兵打仗时候,火车既不易搭坐,只好暂缓来省。”二姐也曾长时间在开封,她的儿子济世、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儿维世,也在那儿念过书。那时候其乐融融的。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十几岁时,听说父亲在外面包了一个女人——就是现在说的包二奶那种。那个时候,男尊女卑,社会和家庭对男人的这种做法是接受的。母亲对此却不高兴。
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传统家长(3)
母亲不是老张罗着给父亲纳妾吗?为什么会不高兴?原来,母亲对那个女人有所了解。早在1928年旧历一月一日父亲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这个人:“前娶黄妾,早经遣去。”母亲给父亲纳妾,总要认真挑选品性。这个黄妾不是母亲给娶的,是父亲写那信之前一年多,在外面纳的,还带着一儿一女。父亲自己记载,是1926年。那年我六岁。没多久,父亲自己就把她休弃了。过了好几年,又来找父亲包养她,母亲就不高兴了。
这个黄,是个四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她的儿子叫常喜,比我大。她的女儿叫好妞,比我小两岁。我见过他们俩。俩孩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还在不在,我不知道。可能是黄愿意的,父亲也觉得这俩孩子不错,就同意他们都改姓了任。因此就养着他们了。没几年后,听我父亲说,常喜年轻轻的就死了,黄哭得很伤心。
父亲因为没有儿子,还把我二姐任锐的次子孙济世正式过继膝下,改孙姓为任姓,叫了任济世,填为父亲的嫡孙。父亲写的所有信里,凡提到济世,都是说“济孙”。父亲还曾自己带着几岁的小济世在外做事,他有封信中说:“济孙十分顽皮。局中人杂,今跟我去,恐怕要越学越坏……他近来并不怕我。每当他多嘴多手时,我恨极无法,喝他爬出去,他便伸手作爬形,座客无不大笑。”济世婚后回新蔡居住,父亲也是按嫡孙规格,让他们住在正房。直到快建国了,济世才改回孙姓。
给父亲娶的妾,比如赵,父母亲说“赵妾”,我们说“婶”。休了之后,父母书面改说“赵氏”,口语仍习说“赵妾”,我们则可以不论尊卑,随父母习惯,日常也说“赵妾”了。这位黄,已不是妾,是外人,父母没要求我们姐妹怎么称呼她,我们跟父母亲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