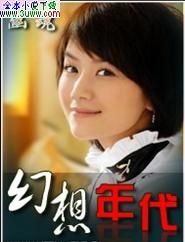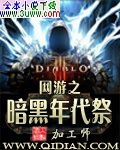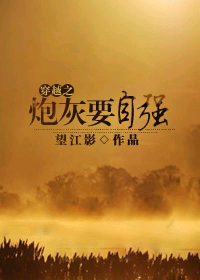七十年代-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花,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净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是永远在这儿呆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农村问题和知青问题,成为手抄本。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任有一拨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6)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北京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辩论,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一门心思全在吃,记吃不记打。
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鸡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我生病在炕,门是破门,赶走一回又来,赶走一回又来。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火冒三丈,顺手抄鞋,嗖,但见门口方向,扑棱扑棱,有只鸡当场毙命。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狗,但骂不离狗。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狗(他的意思是,贱胎孬种,不算人),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乍,我就怕他尥蹶子。
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
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
我记得,队里骟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我呢,“甘居牛后”,两只手紧紧着牛尾巴,比牛更紧张。
手术开始。它稍一抖动,我们就东倒西歪,摔倒在地下。多少次折腾,才把丫骟了。牛蛋,个儿很大,热腾腾,被老韩拿去下酒。我很好奇,不知什么味儿,没敢开口。
记得有回,爬两狼山,有一地儿绝险,两腿打战。
他们那边挺荒凉,却是长城所在。
临走,木生说,我也进城,套个车送你。奇怪的是,他手里拿个蝇拂,好像老道。我纳闷儿,赶车不用鞭子,这算什么家伙?
上路,老牛拉破车,很慢。我说,为啥不用驴。
木生说,我有诀窍,你信不信,说快就快。
他把蝇拂的把儿倒过来,噌的一杵。果然,牛蹬蹬往前蹿。我没看清部位,他说是牛。
但过一会儿,速度又恢复如前。木生说,没事,再来一下。牛又开始狂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7)
如是反复多次,木生很得意。
终于,“咚”的一声,老牛也会尥蹶子,重重踹在车帮上。
它竟掉头狂奔,往回跑。
我们傻了眼。
地下沙龙
冬天,大批知青返城,不管是买票还是扒车。
北京有很多沙龙。所谓沙龙,只是一帮如饥似渴的孩子凑一块儿,传阅图书,看画(主要是俄国绘画),听唱片(老戏和外国音乐,连日伪的都有),交换消息(小道消息)。高兴了,大家还一块儿做饭或下馆子,酒酣耳热,掌而谈。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吃饭最明显。
当时的我们,都是“时间富翁”,不但时间富裕,还不吝时间,走路、骑车,一嘣子出去几十里上百里,一点不嫌累,一点不嫌远。那时,串门经常是挨家串,串哪家是哪家,闲聊神侃时间晚了,干脆睡在人家。最近,我读《顾颉刚日记》,发现他老人家也这么串,家里常有客人留宿。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电视、录像机,那时还不普及。当时还没有这类叫人失魂落魄挨家傻坐只听不说干瞪眼的法宝。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
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当时的我们,让现在人一说,什么娱乐都没有,忒无聊。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有不少可玩的东西,别看不起眼儿,其乐无穷,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简陋是简陋,乐子一点不少。要说缺什么,我看是外国电影。
我记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不乏外国影片,除了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的片子都有。后来,越来越贫乏。大量的资料片,特别是法国、意大利的风格片,有人临时配音发套票的那种,我们是“*”后才大饱眼福。
那些个冬天,太值得怀念了。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眼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八十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
除了聊天,读书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这种读书境界,后来找不到。
当时,书不好找,大家都是逮什么读什么。但我居然读了不少书。从北京到内蒙,从内蒙到山西,我一直带着书。我还记得,我跟我表哥,翻山越岭,从书店往回担书,是个大雪天。我的书架就是由许多书箱组成。
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史、*党史、国际共运史、“*”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斯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灰皮书、黄皮书,各种古书和文学名著,都是我所热衷。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十九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
反动”的东西,只供领导看,这是特权。我们是占老干部的光。北京老干部多,换外地,不可能。这种故事,没有普遍性,外地同龄人,听了就生气。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8)
书,都是不胫而走。中学时代,我家有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很多人不知道。好像刘静子(插友,后来是女作家)还是张小康
插友,后来是爱尔兰大使),她们跟我借,不知传哪儿去了。我经常上她们点,都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我回山西后,她俩给我来封信,说你丫有什么革命实践,也敢怀疑毛主席。
我们的启蒙是在这一段。
没电话,怎么约会
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
现在,当然很简单,打个电话就得了,当年不行。
我记得,电话普及是九十年代。这以前,电话是个稀罕玩意儿,家里装电话,都是单位装的,只有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才有。我们家,“*”一开始就割走了。大家都没电话。就算哪家有,别人没有也是白搭,你给谁打,谁都没法接。所以事情就怪了,大家是怎么往起凑,我怎么也想不起来。特别奇怪的是,有时人还不老少,住的很远,说到就都到了。
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传呼呗。我觉得,这是记忆有误。他是把后来到处都有传呼的那阵儿提前,安错了历史位置。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
还有人说,咱们那阵儿,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就串门,串门都是直扑人家的门,没人打招呼。这话没错。我还记得,早年学英语,说西方礼仪,学生见教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约会,当时我特不理解,觉得外国人怎么这么事儿。直扑当然太有可能,我承认,但总不能回回都这么扑吧?我半信半疑。
总之,大家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着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总能把消息传到。再不行了,写封信,一两天也到了。还有人说,没准上回见面,就把下回的事定下来了。
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起来?
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
人,真是健忘呀!
诗人郭路生
郭路生是一人物。
今天,已经没多少人知道郭路生了,别说80后或70后,60后都没有多少人。但我知道他,北岛知道他,我们那一代的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我们那一代的著名诗人,括号,地下诗人,没有正式印刷品的诗人。我听说,“*”后,哪一年,北岛给他开过一个会,拿他当“*新诗”的祖师爷,仗义。
大概1968年的冬天吧,我见过路生。他是跟马雅(马洪的女儿)一块儿来的,在花园村木生他爸家。怎么来的,不记得了。
那阵儿,我一直住木生他爸家。木生他爸被机关专政,关起来了,罪名是和早年顾顺章叛变的事有什么瓜葛,他妈住人大,不来。家里没大人,特自由。我们天天下挂面,就朝鲜咸菜,看书讨论,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回趟家,回来发现,他家被封了。我和刘靳延一块儿上的楼,被人盘问。靳延家也是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跟木生他爸一个单位,他特紧张,问他家在哪儿,他不讲真话。
我到木生他妈家,工宣队在开批判会,木生哭了,他妈骂他,叫他不许哭。
他爸自杀了。
花园村,我忘不了。
郭路生很腼腆,一点儿都不牛,不但不牛,还一点儿都不扭捏,特大方。他说,我给你们背首我自个儿写的诗吧,说着就开口朗诵,声音不大,口气透着深情。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9)
他念了两首诗,一首我忘了,另一首没错,肯定是《相信未来》:
……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马雅介绍说,他爱上个姑娘,谁谁的女儿,死去活来,撕心裂肺,这是写作背景。
很多年后,在考古所(社科院考古所),路生来了,跟刘新光(刘靳延的姐姐,我的同事)来的,问我还认得他吗,他说他离婚了,精神不太好,在什么单位看大门。
然后,很久都没见过面。
相信未来
又是很多年后,黄元(北大校长的孩子,见面那阵儿,好像在做生意)来了,说是想学古文字。当年,我们这帮附庸风雅的人,上他家玩过,看画,听钢琴——北京的小圈子里风传,就他弹得好。
他和静子约好,一起吃饭,然后去看路生。
路生特意跑到车站来接我们,等了很久。他说,抱歉,我急着出来,没戴假牙,形象很糟糕。
他家住楼房,就一间,跟好几家伙住一个单元,共用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