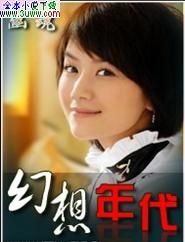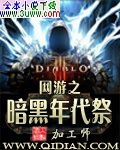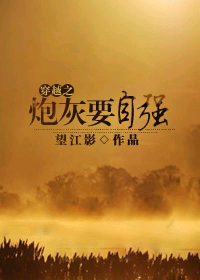七十年代-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家住楼房,就一间,跟好几家伙住一个单元,共用厨房洗手间。
进门,时光倒转,屋里的一切都让你想到过去。家具全是老式,“*”前后才有的样式。靠窗,一张桌子,很小,是他写作的地方,桌上没有电脑。右边有个冰箱,大概只有半米高,是宾馆客房放冷饮的那种。左边有个衣橱。再过来,是张双人床。我记得,屋里好像没有电视。房间太小,什么也摆不下。
天太热,没空调,也没风扇,只有扇子。我问,你怎么消暑。他说,天一黑,他和他爱人就熄灯,静静躺在床上,这样就不热了。
他为我们朗诵,依旧深情。
他说,他每天都写诗,刚才念的是新作。
又是很多年后,路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上庄买了所简易的公寓,农村盖的楼房,要我一定去看他。那边有古建,和纳兰性德有关,他补充说。
我参观了他的新居,比从前好。还看了他说的古建,破破烂烂。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馆吃饭,他坚持要由他买单。
他说,他一直在读我送他的书——他记错了,那肯定是他自己买的。
他说,他还记得花园村,记得木生,有时,记忆力又很惊人。
他说,他很少出门,出门净遇好人,大家对他太好,包括年轻人。
他说,我们要互相加油,看谁更努力,很认真,很诚恳。
我看,他一直生活在过去。但他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未来。
看到他,我就想起了过去。
过去好,是感觉好,唐兄说得没错。
四五事件”
1月9号,广播响起哀乐,一个声音宣告说,8号9点57分,周恩来逝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止不住,哗哗往外流。我不是哭他,而是哭这个国家。
1月11号,十里长街送行,我没参加。我受不了那种气氛,周围人哭,你也会哭。
四三、四四,广场人很多,花圈很多,大家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诗,议论纷纷。诗多为仿毛打油体,半文不白,跟我读过的天地会诗歌相仿,水平不怎么样,但都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诗歌,可以反映民气。
我有点想不到,广场是这样。气氛热闹,并不怎么悲伤。
四五下午,我在场。我的印象,广场人多是看热闹的居多。我开始理解古代的民变。群众自发,是不约而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有个广场,让他们聚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当初修天安门广场,就是为了群众*,地方早就预备好了。古代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10)
事情一开头,大家预感不祥,不祥还是潜在的。大家没想作乱,只是好奇,想去可能出事的地点看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叫“广场效应”。
我也是去看看,跟我老婆去的,到那儿就被挤散了。
那天,天很冷,人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
先头,大家还是聚在纪念碑周围。
有人说,花圈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谣言四起,大家乱猜。
有人说,在中山公园。轰,我被人流裹挟,往前冲。呼啦啦冲进去又呼啦啦冲出来,好像也就一眨眼的工夫(那可是不小的一圈)。我们如一阵旋风,转眼又回到原地。这是朝北跑。
有人说,不,在人民大会堂。轰,大家又一窝蜂冲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一边冲,一边有人劝,千万不要被坏人利用。大家又回到原地。这是往西跑。
最后,又有人说,花圈是藏在历博南侧的小楼,公安部的小楼。轰,大家又朝东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这座小楼。
我看见,历博门口的马路上,一辆汽车被点燃,还有自行车,黑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轮胎味儿。
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
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的场面。“内外有别”,当时说起来,这还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打”(可能是便衣喊的),老外的鞋、帽、照相机就飞上了天。
本来,这人离我老远,根本够不着。但人潮汹涌,如同海浪。一个浪头打来,我就和他撞了个满怀。他不会汉语,只会嘟囔一个词。“毛主席”、毛主席”,他绝望地喊叫,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救他的命。但转眼之间,他又被另一个浪头卷走了。
小楼,有解放军围守,他们手挽手。群众发起冲击,一波又一波。石块如雨,砸碎的玻璃哗哗往下掉。有个战士的头被砸破,鲜血往下淌。群众把他拖出,一边包扎一边说,别打别打,他是人民子弟兵,不能打。
解放军还是个神圣的字眼。
围观的人,有冲在前面的,有躲在后面的,全都议论纷纷。我过去听了一阵儿,谣言夹着揣测。有的说,肯定要*。有的说,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绝不会*人民。
大家都一惊一乍。
僵持中,从历博深处跑出来一拨解放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排着队,双拳握于腰间,夸夸夸,一溜小跑,赶来支援。大家看不见队尾,以为后面止不定有多少人,源源不断。
机关枪”,有人喊。哗啦一下,人潮倒退,全往广场跑。跑到半道,定睛一看,人数有限,哪有什么机关枪。
大家又聚到小楼周围。
僵持终于被打破。有人冲上楼,我纳闷儿,怎么全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好像没发现什么花圈,光是往下扔东西,扔下的东西,无非是桌椅板凳、书报纸张,其中有《毛选》和《语录》,我看得很清楚。
然后,他们点火。火舌从窗口冒出,朝上卷。窗户四周是石头墙,烧不着。我心想,谁叫你们把可烧的东西全扔下来,没燃料了吧。
说话间,没注意,天已经黑下来。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唰的一下,全都亮了。灯柱上的扩音器传出吴德的声音,声音略有时间差,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好像空谷回音。他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劝大家马上离开。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
后来,过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再去广场,往东南一瞥,这座小楼没了,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好像害怕大家再想起这个清明,想起这把火。
但我还记着,记着这最后一幕。
当天夜里,我写了首词,记录我的感受。
在我心中,“*”已经结束了。
2008年6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检讨:
本文经木生审阅,有些记忆不太准确。
1)“木生赶牛”,据他回忆,“牛”有误,“咱们赶的是被骟过的公牛,贫下中农教给我们,老牛皮糙肉厚,就是鞭子打,走长途,它顶多扭扭屁股,还是那么慢。骟牛生殖器两侧的肉最嫩,一捅就会加速度”。伯乐相马,不辨牝牡骊黄。我怎么跟他一样,把性别都搞错了。
2)“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
——记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
1970年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现代西方哲学。1982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1989年移居法国。
一
那是1972年暮春的5月,街头正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我刚从怀柔山中回京轮休,就接到了萍萍的电话,说有个人挺有意思,你来见见吧。傍晚,唐克就背着他的吉他到南锣鼓巷149号来了。
萍萍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萍萍是师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丽的容貌,在我这个青涩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谷的佳人偶落尘寰。她的声音好听,清脆中带着难得的胸音,歌喉宛妙。以她的才识风貌,天生一个沙龙女主人。所以她家那个幽静小院常有各路人马聚会,说的都是中国以外、民国以前的雅事儿。
我那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之时。虽然模样呆头呆脑,但心里满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碍着老辈儿的面子,常常带我玩。这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阶”
胡同里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阶)。萍萍家当庭一棵大核桃树,繁枝厚叶,浓荫匝地,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推门进院,见大树下立着一条汉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宽肩细腰长腿,面色白皙,眉峰外突,双眼下凹,阔额方脸,鼻梁高挺,细看有胡人相。此人长发披肩,一条细腿裤紧绷,屁股的轮廓清晰可见。照现在的说法是“*”,按当时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树干上,右肩上挂着一把大吉他,古铜色的漆皮已经脱落。萍萍介绍说:“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我在工厂看惯了穿劳动布工装、剃着“板寸”的工人师傅,乍一见这副行头打扮的人,颇觉惊讶,觉得有点像港台特务。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来倒不像坏人,显得有点腼腆。
进客厅坐下,萍萍说:“唐克会好多你没听过的歌。”我很好奇,想听唐克唱,尤其是弹吉他唱歌的情形,只在小说里见过。唐克不忙弹唱,反问萍萍:“上次给你抄的歌,你学了吗?你来唱,我伴奏得了。”我这才知道此前他们已经对过几次歌。萍萍说:“你还是先唱几首吧。”唐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调弦。轻拨慢捻,随手给出几个琶音,流泉般的叮咚声就在屋里漾开了。调准音,他回头问萍萍唱哪一首,未等答话,自己就报了名:“唱《蓝色的街灯》吧。”在吉他轻柔的伴奏下,歌声起了:
蓝色的街灯,
明亮在街头,
独自对窗,
凝望夜空。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没有人知道。
谁在唱啊?
远处轻风送来,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哑哑的,但有味道,而且音准极好。唱到高音处,梗起脖子,额头上青筋绷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样子。眼睛只盯着左手的把位,动情处会轻轻摇头。这是什么歌啊!缠绵、忧郁,那么“资产阶级”!在他轻弹低唱之时,我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我们从小只听过毛主席语录歌,那些配了乐的杀伐之声。而这《蓝色的街灯》却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凭这歌声,我喜欢上了唐克。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2)
但唐克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唱完歌,他只是看着萍萍,期待着那里的回应。我忍不住说:“真好听,再唱一支吧。萍萍说,你会很多歌。”唐克仍然看着萍萍,问:“想听哪一首?”问话里含着期待。萍萍轻轻应一声“随便”,便不再说话。唐克低头,只在吉他上摩挲着,不时弹出几个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这屋里,我是多余的。再看唐克,满眼的惆怅,琴声中涟涟流出的全是爱意。没错,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静,唐克突然奋力一击琴箱,随即琴声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转低回,歌词似乎皆从牙缝里吐出,带着嘶嘶的爆裂声: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
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没有人理我,
我也不理谁,
一个人喝咖啡,
不要谁来陪。
我要喝,
葡萄美酒加咖啡,
再来一杯也不会醉,
没有人爱我,
我也不爱谁。
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歌声中的绝望让人心碎。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爱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是总参作战部首脑的公子,家住景山后街军队大院将军楼。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门一带有名的顽主。每来萍萍家,必是锰钢车、将校呢、将校靴,行头齐全。他不大读书,也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真正是根红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么会有话说。
天色渐晚,唐克几次请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应。待他起身告辞,已是繁星满天。我请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给我,他敷衍地应着,显然没想到这几支歌对我的意义。在萍萍那里,这歌是追求者的奉献。在唐克那里,这歌是倾诉爱慕的语言。而对我,却是一个新世界的展现。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门口。月光透过宽厚的核桃树叶泼洒在院子里,天风轻拂,地上满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与唐克相对而立,光影中,这对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刹那,我觉心酸。
离开“高台阶”,陪唐克向锣鼓巷南口走,没几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弯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见,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个门。唐克仿佛猛然醒过来:“噢,咱们留个地址吧,今后好联系。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吗?我抄好就寄给你。”离开萍萍,唐克好像还了魂,说话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才在萍萍家客厅里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见了,举手投足透出几分潇洒。听说他要和我联系,我挺高兴,便把工厂的地址给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两周才回来一次。唐克走了,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微微晃着,披肩发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着,看他消失在灯影里。那不是蓝色的街灯,而是橙黄色的,昏暗、朦胧。后读龚自珍《己亥杂诗》,见有“小桥报有人痴立,泪泼春帘一饼茶”句。那就是年少时的我吧。
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