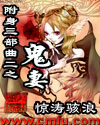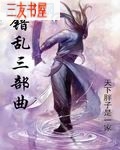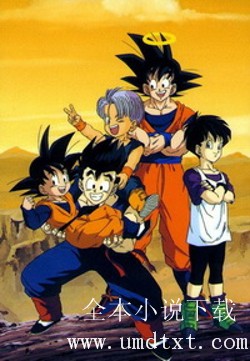旗妞三部曲(望尽天涯路)第一部 正黄旗下-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晚上二老爷一进门就急着问海林:“上头,圣躬如何?”二老爷拽了个文,并习惯的称“上头”,而不是“执政”。
海林苦笑着说:
“什么呀,赶情皇上才三十来岁啊。瞧那样儿还挺精神”,海林可完全用大白话回答。
“你没失礼吧?”
“那哪儿能啊,我跟着宝二爷进去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皇上就问了一句‘你是颜扎氏的后人?’,我回了个‘是’,皇上就从鼻子里‘嗯’了一声,就算准了,宝二爷就把我带回来了。”
“他什么打扮儿?戴王帽吗?”海蕖十分好奇,在她的脑子里的皇上就是那个身穿黄袍头戴皇冠、脚蹬厚底儿靴的老头儿,要不就是《小宴》里唐明皇的打扮儿。
“哪儿来的什么王帽啊?又不是演戏!皇上穿的是西装,脖子上系的是一条红金龙的领带儿!”海林乐了。
“是吗?”二老爷对这事挺感兴趣:
“那是,别瞧皇上不穿龙袍穿西装,可还是真龙天、天子嘛。”溥仪真的还在做他的皇帝梦。
海林也要去上班了,可海蕖依然辍学,公立学校已被日化,春季开学,可打二老爷这儿起就认为那不是海蕖该去的地方,海林也反对,海蕖自己也觉的那是野孩子去的地方,况且不开英文课,倒开日文课。冲着这也不能去呀!那自己到底是什么呢?谁也说不清。长春只有一所教会学教,可教会学校是秋季招生,只能继续等了,海蕖感到了从未有的孤独,没处可去,哪儿也不能去,家里只有新二太太——娘和小脚姥姥,她们很少想到她,她也不想见他们,海蕖唯一能做的就是看书,看瑞表哥送的那本《家》,看海蓉送的那套《安徒生童话选》,再就是写日记,写自己幼稚而孤独的无奈。
海林就职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头,御林军一律要剃成光头,面对着海林的光葫芦,二老爷非常遗憾:
“怎么不盘辫子呢?”
第二件大事是学日文,二老爷又叹息:
“怎么不学点儿满文呢?”
遗憾归遗憾,叹息归叹息,海林还是就职了。护军是私底下的称呼,它的对外名称是“军事训练班”。果然,海林很快就换上了黄军装,可不管怎么着,海蕖都看着别扭,
“三哥,你们一天都做什么呀?光出操呀?打枪吗?”在海蕖仅有的一点点军事知识里当兵就是出操、扛枪、上战场打仗,他是在为三哥担心:
“打谁呀?你打得了吗?”
“傻丫头,御林军是专门护卫皇上的,说白了一半儿是护驾,一半儿是威仪,懂吗?哪有出去打什么仗的啊?”二老爷接过话茬解释说。
“我们呀不光是出操、学《步兵操典》,还学《中庸》《大学》。”
哦,这会儿海蕖好像明白点儿了,她想起了《夜奔》里的林冲,他不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吗?那三哥他们的队伍有多少人呢?不是点名要八旗子弟吗?有那么多人吗?
“哟,三哥,你们有几十万人啊?”
“几十万?哈哈,不零不整,算我在内一共三十六大员!”
“啊?”海蕖一听哈哈大笑,“这算什么御林军啊,这皇上也太小气了吧!”
“你懂什么呀?我们是皇上的亲军,又不是禁卫军,要那么多干嘛!”
“那、那是,皇上的亲军,亲军,有几个人有资格当亲军啊!”二老爷爷颇为得意。
“我们还有一门儿课叫做‘精神讲话’,一个星期一节,今天上午就上了第一课。”海林说着脸色变了,显出愤愤而无奈,语调也变得怪怪的。
“精神讲话?还有这么一门学科?”这回是二老爷不明白了:“讲、讲什么呀?”
“哼,开宗的第一课……”海林顿了顿一字一句的说:“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
“啊”一句话把屋里所有的人都说愣住了。
“那,我们是、是大清的人?”二老爷想了想突发奇想,甚至还带着几分喜悦。
“阿玛,您可真……唉!”海林把话打住了,大家似懂不懂,可心里都觉得沉沉的,不再说话了。
自打到了长春,每逢三节虽然还有债主子上门,可比起肃宁府来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可同时比起肃宁府的节日气儿也是天壤之别了。
这是到长春后的第一个“年”,海蕖已经记不得“腊八”是怎么过的了,原本该是很讲究的正个一个腊月几乎没有任何动静,千篇一律的粗茶淡饭,千篇一律的无所事事,千篇一律的一天又一天:二老爷去发他的纸笔砚墨,海林去出他的操,听他的课;娘和小脚姥姥除了做那口饭之外就没了别的事,娘儿俩不是凑在一块儿瞎叨叨,就是东家进西家出的乱串游,没有了那个贵胄家庭的约束,反倒活得自在了。什么年啊节的原本就没重视过,现在就更必要也没那个条件重视了,对于这位娘来说,除了吃就剩下一样享受不能丢了,那就是那杆烟枪,这也是老两口每天的必修之课,情投意合的享受,卖掉肃宁府的那最后的一点遗产也就在这烟雾中日渐消失了。
年夜饭也不过是炖肉一碗,炒菜两盘儿,祖宗能享用的也只有一盘子馒头,一盘子苹果,新二太太虽然出身于饭馆世家,却连起码的年夜饭的四凉四热都不会做,或者是就没想着该做,更或者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有此一说。什么芥末墩儿、八宝饭、年糕、肉皮冻儿,做起来太麻烦,既然二老爷什么都嫌麻烦,那么二太太也就嫁狗随狗了,干嘛没事找事!
简单的年夜饭后二老爷抽足了大烟上宝二爷家打牌去了,海林也和一帮同事出去玩儿了,新二太太到东屋和小脚姥姥嗑瓜子斗索户去了,只有海蕖没处去,一个人对着奶奶的遗像流泪……
好不容易熬到了秋季开学,海蕖进了长春唯一的教会学校,重读初中一年级。进这个学校没有费什么劲,既不用考试也不用托人情。因为这所学校是英国人办的,一则是很多人不敢去,在日本人一统的地方不进日本人指令的公立学校学日语,却要去学英语,恐有“思想犯”的嫌疑;所以大部分人不敢去、也不能去,小部分敢去的又去不起,教会学校的学费要比一般公立学校高得多,大有今天的贵族学校的意思。好在二老爷还没忘了自己的出身,海蕖才有幸进了这所学校。
终于可以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感觉了,学校依旧学英语、讲圣经,过圣诞节。英语老师是一位英格兰老处女,课上课下都说英语,而且是一个忠实的基督教徒,这三年的学习海蕖不仅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成为了没有受洗的狂热的宗教徒。只有在这个境界里才能找到慰藉,得以片刻的解脱;只有在和老师用流利的英语对话时才能找回一点儿久违了的自尊和童年的梦想。在那些一个个孤独无助的夜晚她有了倾诉的对象,她向主倾诉着自己的苦闷与悲哀,思念与期盼、寂寞与与孤独……
自从得知阿玛续娶的确切消息,海蕖就对这个未来的“娘”有着一种本能的逆反心理,成了未谋面的冤家。在北京的时候海蕖还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许多的亲友姐妹,有熟悉的街道和乡音,有和自己一气儿的佣人,对娘的讥讽和嘲弄还能给海蕖些许快慰。那时候这位新人再怎么不满、再怎么憋屈也还不大敢直接发泄和直接欺负她,现在就全然不同了,海蕖的周围没有了“同盟”、没有了亲友,同时新二太太也没有了那个环境的约束和那个环境给她的压迫,这个家虽简单却真正是属于她的,她现在才真正做了这个家的主人。尤其是海林被派到日本去学习后,她和小脚姥姥就更是肆无忌惮了。二老爷向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管的就不管,能不问的就不问,只要有自己一口饭一个烟盘子就足矣,一切随着太太安排。
海蕖兄妹从来没管这位新二太太喊过奶奶,只叫娘,其实这是对新母亲的始终不承认,因为在老旗人的习惯和规矩中,正经的太太才喊奶奶或者额娘,喊姨太太为姨娘。现在简称新人为娘,也就算是折中一下,已经是给新二太太一个莫大的面子了,二老爷深知其中的奥妙却装作糊涂,不去捅破,也算是对孩子们的一点尊重吧。好在新二太太是汉人,没人告诉她其中的缘由,也就糊了糊涂的答应了。现在这位娘可有权利对这个家发号施令了,在海蕖要去上学的头天晚饭后,娘拿出一毛钱来说:
“我说”,她很少喊海蕖的名字,更不会像奶奶那样亲昵的喊她“妞儿”,好在平时很少过话儿,不得已的时候往往就用“我说”开头:
“我说,打明儿个起就不要来回的跑路了,中午拿上一毛钱在外边儿买着吃吧。”
一毛钱?虽说那时候钱值钱,可也就是俩烧饼钱,海蕖听了一怔,本能的想说什么或者想向阿玛求援,可刚想张嘴就被小脚姥姥堵了回来:
“别嫌少,这儿不是肃宁府,你阿玛挣那俩钱儿够干嘛的呀,还上什么教会学校,能有烧饼吃就不错了。”
一听这话,海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出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突然特别想嬷嬷了,想嬷嬷在她去温泉中学上学时的一再叮嘱和装在网篮里的缸炉烧饼、想阿玛安排的那个送行仪式,想三哥海林送她和六哥海森、表妹颖鸿一起坐大鼻子汽车去温泉中学上学的事了……然而那些温馨的往事已恍如隔世了,嬷嬷现在还好吗?她还挂记我吗?六哥呢?颖鸿呢?他们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又是一个新学期了,温泉中学还是那么美吗?望着这孤独的星空,海蕖的眼泪夺眶而出……
中午同学们大都回家了,教室里只剩下海蕖孤零零的一个人啃着干饼子,校园里很安静,花儿开得正香,草儿长的正旺,一排排的榆树墙修剪的整齐有致,还不时传来几声鸟儿的鸣叫声,初秋的景致挺美的,可海蕖的心情却一点儿也好不起来,反而更增添了对北京的思念和秋的惆怅。
十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两个干饼子怎么能顶一天的生理需要。还没下最后一节课,海蕖已经觉得饥肠辘辘了。放了学急急往家跑,放下书包就奔厨房,刚出锅的窝窝头喷香,炒菜的味儿更是揪人的胃口,海蕖刚要伸手,就听见娘一边儿磕着烟袋锅一边儿走进来:
“哟,几辈子没吃饭啊,跟饿狼似的,还大宅门儿的姑娘呢。你阿玛还没回来呢,这就没规矩了?吃零嘴儿的毛病可不好!”
海蕖一听,二话没说扭头就往外走,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可一转身发现里屋小脚姥姥正抱着点心盒子在吃桃酥。新二太太见海蕖发现了这个秘密,不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冷笑着说:
“别看,姥姥年纪大了,吃点儿偏份儿是理当的。”
海蕖能说什么呢?没人教会她和长辈顶嘴,也没有谁再站出来为她说话,没有了嬷嬷,没有了哥哥们,也没有了去处,只能一个人把委屈和口水一起咽下,只有一次次在脑海里回响着“小白菜”的歌词……;只能一遍遍的向着西南方问天问地问自己:北京啊,真的是“问君归期未有期”了吗?
日子就在这委屈艰辛与无望的期盼中一天天的过去,海蕖也在这一天天的艰难中读完了初中,但长春没有女子高中,海蕖再一次辍学了。十六岁的女孩子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有二老爷的这份薄薪和海林的俸禄,日子好赖总算过得去,而海蕖兄妹竟也因祸得福。长春没有了那般旧亲老友,也没有了“堂会”、“清音”一说,当初的全套锣鼓又都被新二太太三八不值二的卖了,再添吧,既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了同僚,二老爷下班回来憋得难受,实在丢不下的这份“戏情”,在闲极无聊的情况下到成全了海蕖和海林的天赋,这六年里哥儿两几乎把二老爷肚子里的那点儿东西都掏空了:全本的“牡丹亭”、而且是昆曲的,整出的“金玉奴”、“凤还巢”、“穆桂英挂帅”、“玉堂春”、“四郎探母”……,海蕖和二老爷两个人就能全部演下来,再加上海林,父子三人可算是一台好戏了。要说二老爷这一辈子为这个家里所做的贡献,为儿女们所进的责任,除了在宝二爷的关照下拿的这点儿薪金外,就是把这点子本事传给了这一儿一女,以致多年后竟成了全了哥儿俩的一份事业和一碗饭。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还真让二老爷说着了,海林他们到东北没有找到大姐海蓉,却实实在在靠了大老爷一把,大老爷自打从日本回来就步步高升,一直坐到了伪满朝廷的一品大员,自然也就不缺银子嚼过了,看在原配跟前的一儿一女在二老爷府上长大的份儿上,实在不忍让自己的亲弟弟在这荒漠之地遭这份儿罪,再说说起来他大老爷也脸上无光,就这么着,六年后二老爷终于拿着大老爷的“恩赐”和那点子可怜的退休金要“衣锦还乡”了……。 。 想看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