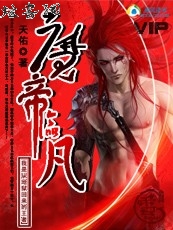网人 作者:黄孝阳-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男生讲,拜托,把嘴张开点,行不?男生愣了下,老老实实咧开嘴。她一撇嘴,唇角上挑,柔软的眼波儿滑过,在他脸上掠过,又迅速收回,鼻尖一耸,露出一丝狡黠之色,哎哟,您老满口大白牙,确实有“齿”得很呢。男生懵了,晃晃脑袋,张大嘴,二颗门牙精神抖擞。他没忍住,扑哧声笑了。女孩儿骂人可真损,不带脏字还拐着弯儿。他瞟了她一眼。她的胸鼓鼓囊囊。她身后有束木棉花,半红半白,浮在沾满尘土的绿叶上,纸扎的般。女孩儿已似笑非笑地转过身,瞥见他,脸上蓦然间泛出红晕,头一垂,玉石的脖颈在他眼前一闪而逝。
他把她的模样放入记忆里,以为这只是一张要收藏起来的相片。没过一个星期,他就在一间小餐厅里又遇上她。她换了一身红裙,艳得像一团火焰,可说话的声音比大山深处流出的甘泉还要清甜。这个比喻有点俗,可他当时确是这么想的。她不小心打翻了他面前的调味瓶,油渍洒了一身。他有些心痛,那是一套名牌西服。他想发脾气,可一眼望见她惶恐的脸,满腔恼怒顿时无影无踪。他想起那天她张牙舞爪的样子,情不自禁地说了声没关系。她涨红脸,说对不起,又小声问,这套西装多少钱?他说,不值多少钱,在地摊上拣来的。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就这样,他认识了她。事情的开始总是纯属于意外。但意外所带来的十有八九与惊喜无关。或者它偶尔会以惊喜开头,譬如这一次,他却总能拧弯它,就像拧开一个水笼头,一些白花花的水珠稀沥沥地滴下来。
他不记得她与自己好了多久。她还是离开了他。尽管他与她一起去看了长城、游了故宫、爬了香山、逛了动物园。他又想起一事。他们一起去十三陵水库,在水坝下的那块绿草坪上玩野了心,结果来时坐的那趟公车开走了。这或许是他们心里一起暗暗渴望的吧。他与她上了水坝,走到石坡下,找了处小林子,两个人相依相偎了整整一个晚上。她说他的怀抱很温暖。她的发丝飘入他鼻子里,有些痒,他打了一个喷嚏,很响的声音。她说这就叫爱情。
他在她送给他的电脑上打着字。心里一片寂静。雨细细地下,把天与地扯在一起。窗口落下一只麻雀,歇在晒衣服的栏杆上,眼睛睁得大大的,身子却一动也不动。他看着窗外,神思恍惚,而天光隐晦,又意味着什么?冥冥中似乎正藏着一只会隐身的蚕,头搁在东南,尾置于西北。其之大,肉眼所不能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蚕的眼里,日月星辰只是肚子里那一根根银丝。他在心底默默地念了几句,把电脑放开。这场雨下得真突然。他这一天都没有出去,就在旅馆里默默地回想过去。行囊里的那几本书都看得有些倦了。这些长短不一的句子会打架。
外面有女人吵吵嚷嚷,不时传来砌麻将的唏哩哗啦的声音。一些音乐在雨声中若有若无地飘荡。罗大佑唱的《童年》。这是否算得上一种天籁?人因孤独,便在自以为是的臆想中,把一些东西称之为能洗得净心灵的天籁之声。这种幻象让他们洋洋得意,以为自己有了用文字随意纂改事实、意淫一切的权力,并傲慢地定义着无知、卑微、渺小,然后自觉已天人合一,得到大欢喜了。腥臭的恶气从他们嘴里喷出,也从扔在床上的这台笔记本电脑上弥漫出来。他胡思乱想着,脖子有点儿酸。他伸手给了自己一记大嘴巴。
22
他在她之后还遇上过几个女子。忘了是在哪遇上的。也忘了是怎么熟稔起来的。人,都是一块块积木,之所以存在,也就是为了在以后的某个时候搭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说到底,无非是一些排列组合。新闻写作一向强调五个“W”,而每个人的故事也都可以用这五个“W”解决掉。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数字,一大堆无比乏味的数字。所谓智慧,也就是玩弄这些数字的技巧,是有钱有闲人喜欢的玩意儿。他不无懊恼地想着,开了房门准备去吃晚饭。中午吃的是方便面,早上什么也没吃。他没有早餐的习惯。这是一个好习惯。能省不少钱。
他看见一只蚂蚁,一只断了腿的蚂蚁正在一口浓痰里挣扎。这是一场生死较量,战况惊心动魄。他不由自主地蹲下身,被吸引住了。为什么蚂蚁就能不屈服疼痛?它一直在动。动作剧烈,左摇右晃,并把头不时地伸入下腹,试图用脖子扛起身体。粘稠的痰液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它的努力。痰是淡青色的,一大滩,里面混杂有饭粒与火腿肠的碎屑。若将它放大几万万倍,样子与一片沼泽地差不多。所以也怪不得这只蚂蚁会在里面精疲力竭。只不过是谁把它的腿弄断的呢?
关于蚂蚁,他略知道些。若把这世上所有的蚂蚁加在一起,其重量大致与地球上所有人体的重量相等。它们是最爱寻衅和最好战的物种。如果蚂蚁掌握了核武器,它们可能在一个星期内毁灭世界。不过,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如果人类消失,其余生物势必繁荣兴旺,但若蚂蚁都消失了,后果却是灾难性的……这些知识都是在一本《蚂蚁的故事》上看到的。
书有点厚。他在一个垃圾筒上发现它。可能被扔下来不久,或许几分钟前还砸破某个男人的脑袋。书右上角有几滴血,颜色鲜红,宛若处子的那个。他仰头瞅瞅四楼某个仍在噼哩叭啪响着的房间,捡起书,看看标价。这书可不便宜,得给人家送回去。他正这么想着,一把椅子突地凌空飞落,呼地一声,擦着额头摔地上了。“嘭”,他吓一跳,赶紧跑,这若再掉下冰箱、彩电、菜刀什么的就不大好玩了。
他把书带回了家。她生气了,说,买这样的东西干吗?他说,捡的。她说,赶明儿去街上捡个大美女来。他说,那比捡书容易多了。开一辆加长林肯,别说捡,美女会自动往车上撞呢。她冷笑一声,你开加长林肯了吗?就算开,怕也是个替人端茶递水跑腿的角儿吧。
她是他的女人。因为结婚,所以两个人现在都心若死灰互相不再有好脸色。说起话来,你一言,我一语,话里多半夹着骨头与兵器。兵器一般由她耍,时不时耍出狼牙棒,而骨头则由他耍,耍来耍去还是天灵盖。他不再吭声,低下头准备去厨房。她把手一伸,说,拿来。他说,拿什么?她劈手夺过他手上的书,弯下腰将它朝鞋柜底下塞去。鞋柜有点重,书只塞进一个角。她尖叫声,死人,还不搭个手。他赶紧过去将鞋柜抬起。她放好书,双手在鞋柜上按了按,眉开眼笑,这书垫脚还正好,鞋柜不再一边高一边低。说着话,白了他一眼,你个死人头,家里的事从来就不用心。他说,那是,那是,我的心全用到你身上了。
她继续白了他一眼,踢了踢脚,趿着的鞋在脚趾头上晃悠了一圈。天气还热。她穿着件小背心,露出白白的颈与好看的曲线。他心痒起来,伸手去抱。她一把将他的手拍开,眼睛一瞪,还不烧菜去?他咧嘴皱眉,诺诺应着,进厨房了。厨房很小,两个人都转不过身。空间逼仄得令人生出无名恼火。他洗了一会菜,胸口愈堵得慌。她已打开音响,在客厅里跳起健美操。一个男人的声音顿时将房间的每个角度塞得满满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换个姿势,再来一次;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专心致志,贵在坚持……”他把菜重重甩入水池,水溅出来,溅了满身。他搓了几把手,用毛巾擦干脸。墙壁上有面镜子,还是房东留下的,经过这么多年烟熏火燎已经变得油腻腻的,从上面刮下一层油,估计也能炒盘青菜。他凑过身,用力挤出鼻尖的一粒粉刺。有点疼。鼻尖红了。他都感觉自己眼泪汪汪了。
音乐正在房间里跳着迪斯科,她的胳膊与腿扭来晃去,与商店橱窗里那个疯狂的变形娃娃差不多。他回过头看了一眼,扭回头朝水池里吐出口唾沫。唾沫被水冲散,一丝一丝,像一张被风撕破了的蜘蛛网。他嘟囔着,真他哥的鸡巴。这句话是她近年来的口头禅。她说这话时总一脸不屑,像吐出片瓜子壳,上嘴唇皮一碰到下嘴唇皮便迅速弹开。她似乎忘了自己曾在床上夸过那玩意儿是一根铁棒。也难怪,哪儿会没有铁棒呢?何况现在物质文明如此发达,就是找一根会跳舞的还穿着天鹅绒的铁棒那也不是难事。
他的目光落在水池边,上面有一只蚂蚁。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摁死它。但很快又出现了两只,他仍毫不犹豫地摁死了它们,可没过一会儿,水池边再一次出现了三只蚂蚁。他叹口气,将脑袋搁在窗台上。窗台是铝合金的,形状规则,不过外面的防护栏就犬牙交错的,若有谁想从这跳下去,怕只会死无全尸。他沮丧地望着窗外,随手舀起水将蚂蚁冲入下水道里。
吃饭的时候他与她聊天。她一翻眼珠子,没理他,自个儿进了房间,过了十几分钟,换了身晚礼裙,娉娉婷婷一步三摇地走出来,晃了晃手指甲,皱起眉头,这美宝莲咋没光泽了?他这时已洗好碗,正趴在沙发上看报纸,见她这等打扮,喉咙里似被塞下个大鸡蛋,翻了个身,把脚架在沙发上,嘀咕声,也不知道说了些啥,觉得心口闷闷的,赶紧连喘出几口粗气。她仍在研究手指头,目光一转,探照灯一般,射过来,说,你是不是往指甲油瓶里掺了水?他摊开手,撅起嘴,我是干这活的那块料吗?她显然不大满意这个答复,嘟囔着,目光在他脸上游移不定,似乎想在上面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猛地想起什么,尖叫起来,木头,还在发啥傻,快换衣服。
她的嗓音怕有一百分贝,窗户上的尘土哗啦啦一阵响,他几乎条件反射般地从沙发上蹦起来,像有人拿针筒在臀部扎了下,脸上泛出一层青白。她已手忙脚乱地从柜子里捧出一大堆衣服,斜眼睨着他,嘴里念念有词,这件大了,这件小了,这件领子不挺,这件袖口磨坏了,丫的,你就不会有一两件好一点儿的衣服?穷里又不是没钱,特意把自己整成这个穷酸样,咋叫我拿得出手?
这话让他感到委屈了,可还来不及分辨,她已把一件圆领针织衫劈头盖脸地套下来,他眼前一黑,下巴顺势就顶在她胸口,刚抽了下鼻子准备享受下女人乳房的香味,她已飞快地拽下这件圆领衫,弯腰,翘臀,脚尖一勾,挑起件黑色茄克,捉着他的左手,往袖套里塞去。衣服斜斜地挂在他肩上,她屈膝在他双腿间轻轻一撞,死人,还真以为自己是少爷的命?起来,自己穿。说着话,风风火火地卷起地上的衣服,一甩手,抛到内屋床上,转过身,见他仍慢条斯理,声音高了几度,你丫在床上蹦达时倒是猴急得很,现在倒像个钓鱼的姜太公了。
他把右手套入袖套,顺便把被团成一个鸡爪似的左手舒展开,苦笑一声,说,那是你魅力大。这是要上哪打家劫舍呢?也就这么片刻,她已将口红在嘴唇上涂过两圈,脚上也套上了鞋子,右手飞快地抓过沙发上的坤包,左手拎起他的胳膊,一把将他扔到门外,一侧身,脚跟往后一磕,门咣当声关上了,然后拽着他一口气飞奔到大街上,拦住辆车,跳上去,这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师傅,去人民东街的“万紫千红”。
去干啥?一头雾水的他好不容易喘平气,瞧着她的脸直发愣。一大团夜色从车窗外掠过,几根电线杆孤独地把手伸入空中。没有麻雀。几盏粉红的灯光却在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灯下一群浓妆艳抹的女孩正匆匆忙忙地向着车流抛着媚眼。他精神起来,挺直身,聚精会神地打量起窗外这些女孩儿的身材容貌,一些光线笔直地刺入他眼里,人影晃过来,晃过去,晃得人晕头转向。他眯起眼,猛地觉得胸口那块“闷”在刹那间就已涨大了好几倍,而喉咙里那颗一直没有消化掉的鸡蛋里忽然爬出一只毛毛虫。
车子曳然而止。他推开车门,哇地一声干呕起来,鼻涕眼泪却似杂货铺里被打翻的调味品,呛得额头又冒出金星。他小心翼翼地擦去鼻腔里喷出的饭粒,又连打几声喷嚏,仰起头,冲着旁边的她歉意地笑,不好意思,不知道咋搞的,可能是流感吧。你等等,我这就去买包餐巾纸擦擦脸。她的脸色早已铁青,一会儿看看停在路边的车,一会儿看看正弯着腰满通红的他,不时抬头望向街道的另一头,目光中的焦灼估计能把一锅水煮沸。他伸手在她手上碰了碰,听见没?我要买餐巾纸,给我一块钱。她顿时似被蝎子螫了口,别碰我。你咋这么不讲卫生?餐巾纸有个屁用,衣服上到处都是污秽,擦得干净吗?天哪,我怎么会摊上你这么一个祖宗?!吃饭的时候叫你别喝凉水,你偏不喝,这下好了,吐了吧,开心了吧,丢人现眼了吧。
他都有些莫名其妙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她说,我倒要问你肚子里打的是什么主意?是不是知道要去“万紫千红”就故意吐,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来?自觉汗颜配不上那儿,所以没脸去?我都没嫌你丢人,干啥要朝我摆出这副嘴脸?你看看你自己,我对你说话,眼珠子却到处乱转,惦记着看路边的小姑娘?我告诉你,看也是白搭,你以为看上几眼,人家就会脱下裤子让你白嫖?也只有我这样傻的,当初才会瞎了眼。他没顶嘴,讷讷地站在一边。那个司机正探头探脑往这边看,他便喊,师傅,麻烦你等会儿。等个屁,她接过嘴,大步流星走到车边,拉开坤包,递过一张十元的,说道,不必找了,然后扭回头,冲着他就喊,不去了。他说,干啥不去了?她说,不去就是不去,你管得着吗?他说,那你刚才疯疯癫癫拉我出来吹风啊?
她没吭声,往旁边走了几步,再走回来,走到他身后,猛地抬起脚朝着他的膝盖处踩了下去,说,买衣服去,这衣服不要了。为啥不要?他从地上爬起来,小声问道。她说,脏了,你不要脸,我还要脸。这衣服上呕吐物,就算是个农民也能闻得出来。他说,这是去见谁?这么大的阵仗?她说,你去了就知道。他说,我可不可以知道要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