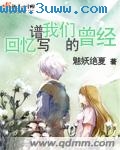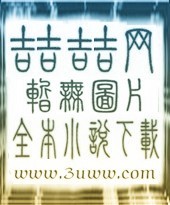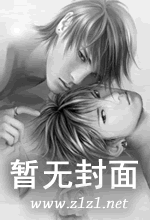回忆父亲聂荣臻-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范济生秘书还记得,五十年代初,有一天,几位老总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开着开着,彭德怀、陈毅突然拍了桌子,大发雷霆,批评总参的某些问题。事实证明,那不能算是总参的问题,都怪到总参头上,是不对的。总参的那二十几个人,当时是最辛苦的,整天累得头晕眼花,换了别人,受到这样的冤枉,可能早就跳起来了。可是,我的父亲却一声不吭。会场外的雷英夫、安东、范济生、刘长明等人急得不行。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2)
散会了,雷英夫、安东、范济生等人围着父亲,怪他为何不声辩一下。父亲说,彭总、陈总都在气头上,没必要顶牛嘛。再说,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听听人家的不同意见,有好处嘛。个人受点批评误解,算不了什么。
父亲常说,遇到事情,要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不能上下推诿。
父亲的得力助手、担任过总参办公室主任的安东生前曾说过:“聂总是厚道人,老实人,受人误解,甚至代人受过,自己也不去辩白。”
1967年初,“大闹怀仁堂”时,父亲对林彪、江青一伙不分青红皂白,打击迫害干部子弟,表示十分愤慨,他说:“你们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却指责叶剑英,说叶曾经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叶剑英感到奇怪,闲聊中说,他不记得自己讲过这句话。父亲对他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父亲后来专门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这让叶帅很受感动。“二月逆流”的参与者被林彪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后,父亲因心脏病住进医院,叶帅给我母亲打电话,让他转告父亲,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父亲与叶帅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心有灵犀,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前后,国家命运最紧要的关口,他们能够默契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否则,父亲怎么敢让杨成武传话?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一些“文革”期间曾经整过父亲的人,父亲后来也没有为难他们。他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当时情况复杂,黑白颠倒,做错点事,有时难免。
了解一个人需要漫长的过程,就像品一壶老酒,越品越有滋味。父亲大概就是个经得起品评的人。
父亲绝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是非常讲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总是认真研究思考,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也不因有某些因素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当年搞“两弹”,中央上层要下马的呼声很高,父亲认为坚决不能下马,所以他宁可得罪人,也顶着继续攻关,最终坚持下来了。
他尤其注意组织原则,在中央对某一问题有了决定,或有了统一的看法时,他就绝不再讲个人的不同意见,也不对外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保障。
父亲的厚道还表现在,他总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给予别人。老一辈的一些科学家们一直忘不掉,当初筹备五院时,哈军工的专家教授们最早来北京报到,当时五院还没有个正式办公处所,专家们住在哪里呢?父亲一时犯愁了,给专家们租旅馆住,他们坚决不干,大家都以艰苦奋斗为荣,怎么能随便花钱住旅馆?临时找点简陋房子安排他们住下了,父亲深感过意不去,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住处腾出来给专家们住。记得那时母亲和我都支持父亲这样做。我们准备临时去三座门招待所暂住。虽然后来专家们坚决不同意这样安排,让房的事没有成,但是,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却一直记在了心里。
父亲的厚道还体现在严于律己。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叶群当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办公室,也陆续安排了首长夫人担任办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来到我家,对父亲说:“现在首长夫人都回来担任首长办公室主任了,可是你这里的主任还是范济生,范济生已经到国防科委任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你的办公室就让瑞华同志回来当主任吧!”
肖向荣还说:“只要瑞华同志同意回来当办公室主任,一切手续都由我来办。”
秘书们心里也很赞成,因为别人家都是这么干的,顺理成章。可是,父亲考虑片刻,口气坚决地说:“不要回来,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来干什么?”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
就这样,父亲把这件事给顶回去了。母亲一直在中组部工作到退休。
母亲是个老资格,1952年定行政级时,她就是8级干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级干部,半辈子没调过级,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合适,想给上级反映,父亲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3)
父亲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不准我们(包括母亲)随便用公家的车,我记得,五六十年代,母亲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还自己带饭。有一次乘车时,太拥挤了,母亲被挤下来摔在马路边,额头肿了一个包,可她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她对我说:“你爸爸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了,心里也不踏实。”
关于乘车,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五十年代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出自行车去学校赶早自习,范济生秘书看见了,决定派父亲的吉普车送我。我就是不同意,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不好。”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就对警卫员使个眼色,警卫员趁我不备,把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司机怕发动汽车引起父亲注意,叫范秘书等人帮着把车推到街上。我无奈只好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怕被同学发现自己搞特殊,坚决要求下车,然后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去了学校。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惟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惟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回来。她的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几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李继津、李继宣、李继家,还有我姨妈张琪华的儿子周继刚、周继强、女儿周继英,都是从小就在我家生活。他们也是从小就受到我父母亲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稍有不慎,就会挨老人的批评。周继强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个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在新四军五师任职,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在陕南他被叛徒出卖、国民党匪徒趁夜围攻时牺牲,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将姨父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解放初,小继强来到我家,父亲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脑袋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要好好学文化啊!”父亲母亲生活上关爱继强,政治上、工作上却对他严格要求,决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纵。我记得母亲曾对他说:“你是烈士后代,永远不要做对不起革命先烈的事,在部队要服从领导,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好好锻炼自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3天,单位领导给了他7天假,让他回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父亲就盯上了他,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当父亲得知情况后,严厉地说:“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搞特殊,过完节,赶快归队。不能当特殊兵!”结果,继家在家呆了3天,提前归队了。这件事,继家一直记在心里,他牢牢记住了舅舅的话,不能当特殊兵。后来他在部队工作,作风正派,老实肯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
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从没在外面惹过事,更没给父母丢过脸。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作风。他和母亲经常教育我,还有住在家里的孩子们,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父亲曾说,旧社会过年,很多人家贴门联,其中常贴的就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中,“厚”是很重要的一条,是“美德”之一。
每每谈起高级干部的家风,父亲赞扬过陈毅、陈赓两家,说他们两家家教好,孩子们懂礼貌,忠厚传家。意思是让我们学习人家。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和孩子都说过,还在教育她,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他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别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互谅互让,互相尊重,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4)
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父亲就是这么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才从内心里尊重他,服从他。
父亲的厚道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对党,对领袖,对战友,对下级,对同志,对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厚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哪怕是面对一个普通护士,面对一个普通战士,说话时他也非常注重礼貌,不管让别人做什么事,他都要说“请你”什么的,从不颐指气使,指责别人。
也许正因为他是个厚道人,他去世之后,才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念叨他。人们怀念他,为他落泪,并不是因为他当多大的官,也不是因为他是个元帅,而是因为他具有让人感动的品格。
他活了93岁,是最后去世的一位元帅,而且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死前头脑一直清醒,极少犯糊涂。医生说他,脑子像是六七十岁的人。
晚年,他曾经念叨过,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福大命大之人。
有人说他是“仁者寿”。也有人说他是“福帅”。
著名文学家巴金说:“聂帅是个很有文化智慧的人。”
……
从他身上,我还悟出:一个人必须多做事情,为民族为国家多做事情,做出好事情,人民才不会忘记他。
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
1999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也是建国50周年。这个时候,我很想替父亲做点事情,更想替国家做点事情。想来想去,我想到,在庆祝建国50周年的时候,如果能够大张旗鼓地表彰一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借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它必将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父亲的后半生,一直寄情于我国的科技事业,主要是抓出了两弹一星。当年,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应该大书特书。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30多年之后,那些为国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仍然鲜为人知,仍然默默无闻,我觉得应该到了让人们知道并记住这些无名英雄的时候了。把两弹一星的精神弘扬光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如果父亲活着,一定会支持这样做的。
有一天,我在参加一个活动时,碰到朱镕基总理,把自己的想法简单讲了一下。朱镕基认为有道理,可行。他当时很忙,就预定了一个时间,约我再去细谈。
不久,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约我和丁衡高一起去与朱总理面谈。听完我们的想法,朱镕基说:“我个人赞成,是好事。”他提出,让我们再和锦涛同志谈谈,因为他分管书记处工作。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胡锦涛,和他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听完我的具体想法后,胡锦涛也表示同意和支持,并且说:“你就以老同志的名义,给中央写一封建议书,由中央研究后实施。”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封建议书是由我、丁衡高、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一起讨论后完成的。1999年5月4日,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朱镕基和胡锦涛。
信中说——
镕基、锦涛同志:
建国初期,经党中央和毛主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