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4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既不谴责任何事,也不指责任何人,他就是这样鼓舞了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些经过他培养训练的人们,那些所谓“周的人”。他们个个以他为榜样,毫无怨言。“他告诉我们精神是我们主要的力量源泉。没有精神的力量就不可能战胜困难。我们不悲伤,不失望……”“我觉得,那时候,为了使中国能够生存,情况能够好转,就是周总理让我去死,我都会高兴他说:‘是,总理。’”
为了应付严重的食品短缺,周研究了每个工人、教员、坐办公室的人员所需的热量。知识分子要多发些油、糖、肉。工人要多发点粮食,碳水化合物。重工业部门的工人、煤矿工人、炼钢工人受到特别优待。以女工为主的轻工业工厂将一天的工作量分为两天完成。学校的学生上半天学,以便节省体力。要求人们多睡觉,躺着休息。所有人的体重都减轻了,包括周和他的夫人。他们也同样凭证购物,周拒绝从专门供应外国人和高于的商店里买任何定量供应以外的东西。乐观开朗的陈毅掉了 15 公斤肉。他把购货证弄丢了。补发前,只好向朋友讨点东西吃。周请人喝白开水,不再泡茶,茶叶太少了。秋末,颖超把中南海她家院子里的落叶扫在一起,煮汤喝。她把门外站岗的保卫人员叫进屋,要他们”坐下、躺下……节省点体力。”
周恩来说:“由于劳力分配不当,只得匆匆忙忙地收割、打谷……由于缺乏在丰收情况下估计收成的经验,我们正在经历暂时的困难。”
“相信他的话吗?”吴全衡、朱清、康岱沙都是我的朋友,听我这么问都哈哈笑了。“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我们当时必须保持勇气和信心,周讲得最透彻……正是因为我们采取这种态度才渡过了难关。”
华北闹旱灾,华南遭水灾。没有肉、没有鸡蛋、没有豆腐、也没有牛奶……各种生产食品的方法应运而生。学校、工厂、机关、大学和其他单位都组织各自的运输队伍到远处的公社为本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搞粮食。花园、公园、庭院都变成了菜地。城里房屋的阳台被用来养鸡,公寓楼梯上可以看到母鸡。每个窗口都放着种有黄瓜、土豆、西红柿的花盆……周不同意在寒冷的冬天单给他的房子送暖气。他工作时身穿大衣,脖子上围着围巾。邓颖超戴着厚手套,穿着厚棉靴。办公室的暖气每天只供暖两个小时——因为没有煤。
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1960 年 7 月,1390 名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使情况更加糟糕。科技合作的项目全部取消,设备供应的所有合同全部终止。赫鲁晓夫在进行报复。周恩来镇定自若地对迷惑不解的埃德加斯诺说,“苏联专家回国是很自然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在这儿呆一辈子。”①
我四处跑,注意到工业垮了。工厂都不冒烟。武汉的新炼钢厂已停产,和蔼的厂长告诉我说是“大修”。没有饭锅,没有剪刀,没有线,没有火柴,没有纸张。每人的棉布定量减到一年一米(婴儿每人 15 米)。
1960 年底,周与已故的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一起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中。他重申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与美国没有利害冲突……我们愿意谈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他讲话的口气显示他完全掌握国内外的局势。采访后他问格林:“你为什么那样忧心忡忡呢?你所提的问题都表现出一种忧心忡忡的心情……瞧我,我比你年纪大得多,可我就不那样,你又何必着急呢?”
不着急,他是这么说的。但那年冬天我和他在他家里交谈时,他并不想粉饰当时的真实情况。屋里非常冷。我穿着皮大衣、靴子,戴着帽子。周穿着两件毛衣,但没穿大衣。他又瘦了许多,衣领显得过大。他的身上迸发出一种无形的但可感觉到的内在力量,整个房间都充满生气。我们两人喝着热开水,他说话时没有看我一眼,象是在高声自言自语,不吐不快:“你已经到处走过,看到了我们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不为外界所知的成果。某些人想压我们屈膝讨饶,但我们决不会屈服……某些人以为只有他们掌握智慧,只有他们能够解释马克思主义。我想你已经读了我们的一些文件。”
我读过了。一场没完没了的理论方面的论战。莫斯科针对中国抛出了长篇累牍的文章,北京则针对“修正主义”发表了声讨檄文。我告诉周,“我现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笑道,“你进步的速度加快了……”他还记得我 1956 年说过的话。他用英语说,“最好慢而稳,不要操之过急。”当时正在上映一部有关列宁的影片,讲的是 20 年代初俄国发生的饥荒。“列宁没有屈服,他从未悲观失望。”接着他讲了很多有关经济的情况:商品短缺、工作中的缺点、取得的成就……他让我如实地告诉他在旅途中我的所见所闻。“我们从下边得到的情况并不总是真实的……我们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顺便提一下,他曾问到我知道长纤维棉与短纤维棉的区别吗?不知道。那非到我搞懂为止才放过我。
周恩来谈到猪。农民被共产主义就在眼前的想法搞昏了头脑,杀了很多猪,饱餐猪肉。“我们需要养更大、更肥的猪,要搞杂交……我们要从西方引进大白猪……我们还要改良美利努羊的品种……我们一定要重视饲养牲畜,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发展畜牧业。我们汉族不是牧民,不懂牲畜,只有少数民族懂。”有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大风中不倒伏的矮梗稻,它很适于在中国南方台风影响大的地区种植……第一批生物遗传学研究所正在建设中……“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我们不能照搬别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的土地与人口的基本比例很不协调,可耕地很少……找到我们自己的模式还需要时间。”他又谈到亚、非、拉人民的解放。“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美苏之间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与这些地区争取解放的人民之间的矛盾……我说的解放,也指经济上的解放。”
就在那年令人沮丧的冬天,我也成了“周的人”中的一员。我是指精神上,因为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府或党派。一个工作狂。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许多年来周是这种献身精神的代表。对我以及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周既体现了我们熟悉的旧中国,又体现了我们孜孜以求的未来中国。
调整。农村地区有自由市场、自留地,有机会进行市场经济式的活动。党虽然对农村经济放宽了,却加强了对工业的控制。周在 1961 年 1 月宣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业发展规模应适应商品粮数量以及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数量。”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应按比例增长。砍掉了“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六万个县级和20 万个社级小工厂。
毛提倡的发动群众的做法已被摒弃,关闭小工厂打击了普通老百姓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要管好经济,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县里甚至公社都办了大大小小的化肥厂。周最艰难的任务是使城市人口不要过度膨胀。任何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都要送回农村,总共遣送了 3000 万农民。周支持毛的计划,把官员送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他到河北省搞了两周的实地调查,又回到 1957 年他受批判时曾呆过几个星期的县里。他从那里给毛打了电话,汇报县里公社的情况。(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纽。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这样,周恩来、陈云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开始了他们的重要恢复工作。他们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了解周的人谈起他那几年的工作时说道:“这是一出空城计,他成了诸葛亮。”
也许周是对的,他说“精神力量”是遭受灾难时决定胜败的最重要因素。中国的情况得到改善,比预计要快得多。最重大的胜利是东北大庆油田的开采,大大减少了中国对苏联石油的依赖。兴高采烈的周恩来在油田呆了五天时间,向参加油田会战的 5000 多名复员军人讲话。另一个令他兴奋的原因是聂荣臻谨慎的估计。“恩来,有可能在两年内我们便能解决核能问题。”1961年周恩来和他的经济学家着手一项重要任务是重新部署中国的贸易格局。脱离苏联,接近西方国家。在一次有关经济情况的讲话中,周提到向莫斯科偿还债务的问题。1962 年他说,“我们已还清了大部分。只剩下很少一点了……我们现在要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
这点能做到吗?
实际上很难。因为美国 1951 年实行了禁运。对中国实施的战略控制要比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严得多,而且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都追随美国。针对中国的三个禁运货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全面禁运一切武器、弹药、作战装备、原子能材料、机械设备、原材料、精密仪器如具有特殊用途的显微镜、工业设备;一汾对各种商品包括医药用品的管制,一个罗列 200项的特别单子,包括对金融、运输和燃料储藏设备的限制。但是欧洲国家对这些限制开始表示不满。西德和英国商业集团已经悄悄地与中国进行进出口贸易。
周恩来一度对美国新总统约翰肯尼迪抱有希望,指望他能以新的眼光看待美中关系。他有时显得对肯尼迪有点着迷。“你能告诉我有关他的情况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周在重庆时结识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谈起新总统来眉飞色舞。周问我“为什么?”我给他寄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书,包括一些年后我寄的大卫哈伯斯塔姆的书《出类拔荤之辈》。周很欣赏这本书,让人把书译成中文。到 1963 年为止,周还相信如果他能了解肯尼迪、了解肯尼迪的性格的话,也许中美双方会开始对话,而作为中国生命线的贸易便可能得以改善。周说中国愿意向美国开放市场。美国西海岸的商人们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不能进入中国市场很不满。当周的朋友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1962 年 10 月下旬访问北京时,周与他详细地谈论了肯尼迪。周说:”中美之间没有利害冲突,这与某些国家的情........况不同...……这点美国总统意识到了吗?”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对我说:“他好象很不满意肯尼迪。有时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抱怨。我想他原先期待着某种信号,希望禁运有可能有所放松。现在他似乎觉得肯尼迪太愿意听苏联人的了,不理睬中国。他也许说对了。”甚至 1963 年 7 月 17 日,周还对肯尼迪现象表示不解,还问班纳吉代办:”肯尼迪究竟哪点与众不同?”“他有魅力,他年轻有为……”周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说话象个傀儡。”很快,他道歉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可大家部象你这么说。一点也不具体。我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1960 年和 1965 年之间在我与周的四次会晤中,他几次提到肯尼迪“身边的顾问太糟了。”他的焦虑是肯尼迪的所作所为引起的,特别是肯尼迪对刚开始的越南战争的态度。
如果有什么因素会使中美互不来往的关系变得更糟的话,那就是越南的军事冲突以及将越南的好战态度归咎于中国,但这正是肯尼迪的某些顾问的看法。周说,“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好战。他以为在进行一场小规模的、能够控制的战争。”1961 年 5 月 10 日,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五角大楼的要求,在越南迅速部署美国军队。除了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以外,肯尼迪的大多数助手都叫嚣着支持向越南派兵。肯尼迪在灾难性的出兵猪湾中受到心理创伤。他将于 6 月 3 日在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他要表现出强硬、有胆量……周可以理解这一点。但他主要责备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五角大楼的鹰派人物。“他们称中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根本不懂历史。”总统手下的人的fan华大合唱,影响之大连头脑清醒的一些人都受到感染。埃夫里尔哈里曼把中国说成“对全世界的威胁比苏联更大。”历史学家费正清本应更清楚实际情况,却争辩道,“在朝鲜边界、台湾海峡以及越南..等问题上都不能很快取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
但是周从他这方面正在尽一切力量来“遏制”逐步扩大的越南战争。中国肯定不会反对越南实现统一的目标。由于美国支持的甫越政权破坏了日内瓦协议,1960 年 12 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党代会的一次会议上,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一起作出了用武力实现越南统一的决定。“解放南方与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是同等重要的任务。”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中国有义务提供援助。周曾许诺帮助他们。然而,周很慎重,没有派中国志愿军。“越南人民通过人民战争,通过持久战,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国土。”这是指打低调的游击战,慢慢消耗敌人。不是声势浩大的正规军事行动。周是不是希望肯尼迪已经注意到并明白了中国谨慎地对越南提出忠告的意图呢?就在这些年里,中国的贸易开始转向西方、转向大洋彼岸。虽然赫鲁晓夫 1961年已经发来信息表示和解,中苏贸易还是急剧下降,到 1964 年,两国贸易往来几乎减少到零。
周与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交锋是在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上。全世界的共产党代表云集在克里姆林官宽敞的大厅里巨大的水晶灯下。周率领中共代表团赴会。几乎没有人来同他握手。阿尔巴尼亚是中国与“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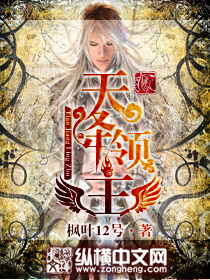


![[快穿]我是他的未婚妻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23/2329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