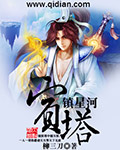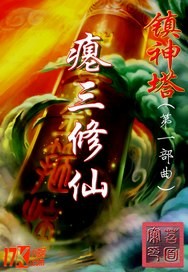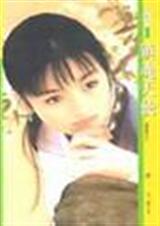南河镇-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封死通道并压以重物。顶层放有砖头瓦块,有的还放有火器并留有枪眼,以便居高临下地打击土匪。
佘有志给他的新居取名“佘福庄”。房子还没干透,佘有志便迫不及待地搬进了他的佘福庄,并将所有的浮财和批量的烟土,也偷偷地转移了过去。除团丁外,他还在新居中养了四五条狼狗。
凭着坚船利炮,列强们终于打开了中国封闭了多年的大门,西方文化也于不知不觉中渗了进来。年轻的举子们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受着西方文化与西方的文明,并用新思想新眼光思考着审视着中国的国情,同时还在不断地探索着寻求着强国之策与救国之道。陈德润便是其中之一。
与一般人相比,读书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陈德润发现在短短的六十年中,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定的城下之盟,竟多达二十余条,索赔的白银,也高达十二亿六千五百七十万两,特别是在前不久刚签定的辛丑条约中,列强索赔的白银,连本带息竟高达九亿八千万两。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不能不陈德润大为震惊夜不能寐,经过反复的思考,他终于对“弱国无外交”的道理,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条教育兴国的计划,在年轻举子陈德润的胸中,渐趋成熟。
陈德润准备创办一所全新的学堂,这所学堂里不但有国学还有西学;在这所学堂里就读的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这所学堂的学子们不必再做八股文章,因为八股文章只能误国而不能强国;在这所学堂里,学子们必须学到富国强兵,与安邦治国平天下的真才实学;这所学堂的名字,应该叫做“南河实业学堂”。
原先之所以先修桥而没有急于办学,陈德润并非是不想办学或者不重视教育,而是对办什么样的学校他还没有想清楚。再说,不修桥解决东西交通不便的问题,就只能收河东堡的那几个娃娃了,而三女河以西包括南河镇在内的,几十个大大小小村庄的孩子,都将因交通不便而被拒之于校外,那还能叫做“南河实业学堂”么?
关中人习惯把吃晚饭叫做“喝汤”。喝罢汤,陈德润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老秀才,岳父老神仙和妻子孙兰玉,大家一听无不击节叫好,老神仙感慨地说:“还是润儿想得长远,果然是后生可畏。”老秀才则更加激动:“渭河南没有学堂的历史就要结束了,我们秀才家人老几辈宿愿,终于指日可待了。”
“不对!”有人突然插入的一句话,使众人不约而同地吃了一惊,回头看时,才发现是菊儿一家,而插话的,竟是谢铁成。
“铁成,有什么不对,快说说你的高见。”陈德润惊讶地说。
“论打铁擀面,咱还凑合一二,这舞文弄墨的事,咱可是行外,又能有啥高见?我是说伯父他说得不对,眼下的陈家,已不是秀才家而是举人家了。”谢铁成笑道。
“凭秀才家。。。。。。不对不对!凭举人家的声望,我看这件大好事,肯定能办成。”菊儿也附和道。
“烧水打铃看门,就包在我的身上咧。保证误不了事。”坐在轮椅上的郭福寿也接茬说道。
“福寿,你的心也太沉了,一个人就占了三样。这女子班你包不包?不包可就归我了。啊——”一直插不上话的孙兰玉,这时却打趣地说。
孙兰玉的一句话,把大家都惹笑了。陈德润笑着说:“学校办成了,大家谁也清闲不了。说起容易做起难,目下八字还没见一撇,有许多具体问题,譬如资金问题,校址问题等等,咱们还得仔细商量。回去大家先慎重考虑一下,改天咱们再议。”
这天一大早,陈德润和孙兰玉被菊儿从睡梦中喊醒了,说郭福寿有急事要跟他们商量,陈德润忙问她有啥急事,得到的回答,却是一阵越来越远的脚步声。
跟在陈德润后面,孙兰玉连颠带跑急急火火地赶到郭家时,却见郭福寿正漫不经心地翻看着一本旧书。知道没啥急事,陈德润跟孙兰玉这才放下心来。
“福寿,你啥时候变得如此的用功?”陈德润打趣地说。
“福寿,你是属鸡的?起得这么早!”孙兰玉也嗔怪道。
“他呀,又犯神经了,昨晚他压根儿就不曾合眼。来,你俩先擦个脸吧。”这时,端着洗脸水的菊儿正好走了进来。孙兰玉跟陈德润的确都没有来得及洗脸,但夫妻两个却面面相觑着,迟迟没有动手。
“昨晚你的一句话,把我给提灵醒了。办学不是正需要资金吗?我突然又想起了这本书。”对陈德润,郭福寿解释说。
在菊儿过门三天后的一个晚上,老财东突然把儿子郭福寿叫到家里的神龛前,在严肃地点燃蜡烛又上了三炷香,并带着郭福寿在列祖列宗面前三叩九拜之后,老财东才拿出了一本书庄重地对郭福寿说:“福寿啊,这可是咱老郭家的传家宝,你爷就是这样将它交给我的,并说解不开交时它能帮上大忙。如今你已成家立业,按你爷的吩咐,我今天再将它交给你,你可要藏好千万不敢弄丢了。等你的儿子成家后,你也得按今天的规矩再传给他。记住了么?”由于心里紧张,郭福寿庄重地点着头,用不住颤抖着的双手接过了这部书。后来郭福寿偷偷把这本书一页一页地翻了好几遍,除了几行手写的打油诗外,并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昨晚他又让菊儿把它拿了出来,并琢磨了一宿,却还是没有琢磨出什么名堂来。
郭福寿把书递给陈德润说:“你读的书多,帮我看看,看里边到底有些啥名堂。”陈德润接在手里一看,发现是嘉庆年间出版的一本《本草纲目》,于是心里已明白了几分。秘密,秘密很有可能就在那几句打油诗上,因为椐陈德润所知,郭家各种版本的《本草纲目》,少说也有五六本,其中还有康熙年间的。于是他直接找到了那首诗。
榆钱落树下,柳絮飞上天。
椿香随风去,槐花落水间。
陈德润反反复复地诵读着这首半俗半雅的打油诗,并仔细推敲着其中的每句话和每个字。瞅着陈德润,郭福寿、孙兰玉跟菊儿,在一旁焦急的期待着。
“家里是不是有四棵老树?”陈德润突然问郭福寿道。孙兰玉跟菊儿也随即将目光移向了郭福寿。“后院里树多的是,远不止四棵。”郭福寿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说的是老树,至少有八九十年树龄的老树。其中有一棵是榆树,一棵是柳树,一棵是槐树,还有一棵是香椿树。”陈德润进一步提醒郭福寿说。
“差不多,好像差不多。到后院去看看,不就都清楚了?”陈德润的提醒,倒让郭福寿费了些思索,他闷着头想了好一会后,才似是而非地回答道。
第八章郭福寿雪中送炭 佘有
陈德润推着郭福寿,与孙兰玉和菊儿一同到了郭家的后院。正如郭福寿所言,后院里各种杂七杂八的树木确实不少,但仔细看时,跟水桶一样粗的大树,果然只有四棵,而且正如陈德润所言,一棵是榆树,一棵是柳树,一棵是槐树,还有一棵是香椿树。于是三双惊呀的目光,又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陈德润的脸上。郭福寿则更为惊讶:“在这院子里,我出出进进了二十多年,都不曾注意到这些,你咋就知道的这么清楚?”菊儿却不无失望地说:“几棵老树能值几个钱,也算是传家宝?”陈德润却不以为然地说:“其它几棵树确实值不了几个钱,惟独这老榆树,却不可小量。”孙兰玉焦急地催促丈夫说:“你就别再卖关子了,快说说看。”郭福寿跟菊儿也异口同声地附和着孙兰玉。陈德润笑着说:“不是我卖关子,而是你们太着急又光打岔。这首诗中写得明白,柳絮轻飘飘的,飞上天自然是无影无踪了;这香椿虽香,却也随风而去了;这槐树又长斜了,树冠已伸到后墙外的水沟里,槐花自然也随流水漂进了三女河;惟独这榆钱不轻也不重,落在了树下,榆钱——余钱!余钱不就是余下的钱么?”
三个人顿时恍然大悟。郭福寿着急地说:“咱们现在就挖,看看老祖宗到底给咱余下了多少。”郭福寿一面说一面教菊儿去拿镢头,菊儿刚要转身,却被陈德润给拦住了:“这是你们老郭家的秘密,道破天机实属万不得已,这后面的事,我们说啥也不能再掺和了。恕不奉陪!兰玉,咱们走。”说完陈德润跟孙兰玉转身就走,左拦右拦,菊儿却连一个也没拦住。
是话不是话,提起了放不下。喝罢汤,就办校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济生堂里又是一片议论纷纷。老秀才和老神仙说济世堂先拿出一千银子,作为启动资金,孙兰玉说她也拿三百两。“不用了,资金,我全包了。”一听是郭福寿的声音,老神仙和老秀才不禁大吃了一惊。望着刚被菊儿推进门的郭福寿,两个老人疑惑地说:“福寿,你碰到赵公元帅了?”不等郭福寿开口,跟孙兰玉相视一笑后陈德润对两个老人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大家能看到的,只不过是些浮财,哪个会把黄金白银明晃晃地摆房梁屋脊上,等着贼偷土匪抢?请二老不必多疑。”孙兰玉也笑着说:“福寿,看来你不必再抢着烧水打铃看大门了,你就准备当你的校。。。。。。”“咣当”一声,孙兰玉的话被打断了。将一包散碎银子墩在了桌子上后,谢铁成不好意思地说:“手头不宽裕,我凑凑合合地搜腾了一百两银子,添不了斤,咱添个两。请大家莫要笑话。”孙兰玉却取笑他说:“铁成,你晚了一步。校董,已被福寿给抢走了。”
老神仙和老秀才不明就里,几个晚辈的话又如打哑语,两个老汉更加糊涂了。他们先用目光互相探询了一眼,期望着能从对方那里得到诠释,但所看到的,却是对方的一脸的茫然。将那一百两散碎银子重新包好后,菊儿递回谢铁成手里说:“学堂要办,面馆也要开,济世堂不但不能受影响,还要扩大。你们的钱先放着。”又是咣当一声,两根黄灿灿的金条被菊儿放在了桌子上,“这点钱先用着,不够了再说。”这咣当一声响,这两个黄灿灿的金条,还有菊儿那说话的口气,不光使两个老人,就连陈德润孙兰玉和谢铁成,都被惊呆了。陈德润和孙兰玉虽然知道“榆钱落树下”的秘密,却没想到这“余钱”竟然还是黄货,听菊儿的口气,还远不止这些。让人最担心的经费,看来已经不成问题了。五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一时没有了话,刚才还你一言我一语的热烈气氛,一下子凝固住了。
“不说明来路,这钱咱不能用。”老神仙终于打破了沉寂。“对对对,眼下咱们需要钱不错,但须取之有道。”老秀才也附和着。“两位大叔,这钱绝对是干净的。大家就放心地用吧。”郭福寿解释说道。“福寿说的是实话,至于详情,回头我们再给大家慢慢说。”看了丈夫陈德润一眼后,孙兰玉帮着郭福寿说。“对对对,详情咱下去慢慢说。要议的问题还多,咱们再说说校址吧。”陈德润岔开了话题。听了孙兰玉的话,众人心里不觉塌实了许多,见陈德润又提到校址,于是又纷纷的议论开了。
“就放在桥头吧。先生们的饭,由我来管。”谢铁成胸有成竹地说。“我看不行。你的饭馆太小了,先生们吃饱了,娃娃们却还饿着。咱们的学堂里,得有食堂。”孙兰玉说。“不但要有食堂,还要有宿舍。要办咱就办得有鼻子有眼,学生娃有处吃没处住也不成喀!”郭福寿说。“对,福寿说得非常好!咱们的学堂,应当办成一流的。目前是个小学堂,将来说不定要发展为中学堂甚至大学堂。办学首先要方便学生,依我看放在河西堡附近比较合适,那里位置适中,交通也方便。不知大家以为如何?”陈德润的设想,竟是那样的远大和宏伟,大家的情绪又一次地被推向了高潮,于是众人异口同声地投了赞成票。
虽然也投了赞成票,谢铁成却多少有些丧气地说:“把他家的,弄了一整,连个厨子都没争上。”郭福寿却诙谐地说:“铁成,你的手艺,瞎不了。等一开工,你就来给匠工们做饭,咱们再给你挂个牌子,就叫做‘桥头面馆河西堡分号’,你看咋样?”还没等谢铁成作出反应,陈德润又接茬说:“诶,这匠工还确实是个问题,不光手艺要好,人品更要端正。菊儿你。。。。。。”见陈德润问到她,菊儿忙回答说:“哦,你交代的事,我已跟俺爸提说咧,俺爸说。。。。。。”刚一开口,菊儿也被人打断了。“匠人的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了。”
回头看时,大家这才发现是菊儿他爸老木匠,紧跟在老木匠尻子后面的,是刘子明跟马子亮兄弟。
“嘴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人都说陕西地方邪,果然一点不差。兄弟,来,过来坐下说。”老神仙和老秀才笑呵呵招呼着老木匠父子,众人也纷纷起身让座。
“四匠由主,是土混还是砖混?让我心里先有个数。”刚一坐定,老木匠就提出一个大家都不懂、当然更不曾想到的问题。
盖房子的学问,也不少。那些大户人家盖房子一般都是三间,中间是通道,两侧为卧室,叫做“一明两暗”。
其中一坡流水的叫做“厦子”,也就是陕西八大怪中所说的“房子一边盖”。厦子房只有一坡椽三道檩。椽长一丈三尺,叫做“丈三椽”。椽的大头因粗壮而要富态得多,所以无论从力学角度还是美学角度看出发,大头都应当向下。椽留在屋外的部分叫做“檐子”,“檐子”一般长三尺,最短也不能少于二尺八,少于二尺八就有失协调而且显得小气了许多。屋里虽然还留有一丈,但水平长度实际上只有九尺。三道檩中最低的那道因搁在檐墙上,所以叫做“檐檩”;最高的那道因搁在背子墙上,所以叫做“背檩”;中间那道因横担在椽的腰部偏上处,所以叫做“腰檩”。“腰檩”不放在椽的正中而放在偏上处,是因为越往上椽也越细的缘故。“檐檩”跟“背檩”下面虽都有墙支持着,但“檐檩”却要比“背檩”粗壮而且端正得多,因为它毕竟在人面面,因此必须富态些,才显得体面。
两坡流水的叫做“大房”,大房按进深的又分为“鞍间”、“楼房”和“庭房”。
鞍间房的特点是前后檐各一坡丈三椽共五道檩,其中“檐檩”和“腰檩”各两道,屋脊上的那道檩叫做“脊檩”。因悬空而且要供两坡椽共用,所以“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