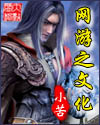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黄巢入长安,未能乘胜而击退却至川的唐朝廷,结果留下后患,数十万大军流动作战,并没有做好得天下之后的战略准备,没有开思想会,也没有开动员,而是让流寇主义作了主,思路决定了结果,所以二年之后,黄巢便再度兵败退却,最后于884年夏天在泰山虎狼谷以弹尽援绝而结束,前后十年,风云际会,可谓是布衣撼动天下的首举。
黄巢起兵时自称为“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表达出他的起兵理念,也是黄巢对当时朝廷的昏庸暴敛而至的民众贫苦而表达的自主均平的民众思想。而自此之后,“均平”这一思想便渐渐演化成为“均贫富”,成为了中国后来历史中出现最多的民间变革的思想核心。在漫长的封建专制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专制政权之下,民间物用的贫乏与政治思想的无权之间,物质贫困导致的压迫感自然要来得更加直接,所以“均贫富”便是解决这个直接问题的直接手段。然而,过于集中于这个焦点,这也导致历史上对“贫富不均”背后更大问题的思考的不足(许多人甚至在今天都无法确切知道造成物质财富不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人本的态度来审视,一个社会如果仅仅将均平的标准落在物质标准之中,可以说是对人自身价值的一个极大忽略,同时这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人文思想的一个严重局限。也正因为这一点,造成了中国由封建时代开端而至今天在人文精神方面的整体不发达…即除了物质之外,我们无法发现作为人自身的更大价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裂变:浑沌的能量(4)
这种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上升为对权力的争夺,在后继而来的时代中,几乎成为了中国社会与价值观的主导。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物质化与权力化的价值观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事实上,自唐之后,这种价值观就充斥了中国的全部世界。
五代十国的蠹害
公元907年黄巢的叛将朱温(因招安而被赐予名朱全忠)废掉唐哀帝而创立梁国自立为王时,唐朝就由此而从世界的历史上彻底消失了。自此之后五十年,由唐朝未期###而坐大的各节度使都纷纷轮番登位称王,这个轮番的过程,便是相互杀伐的过程。自梁为始,依次为唐、晋、汉、周,共计五朝,史称为五代,加起来不过53年,然而就是这53年,几乎将自唐而兴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杀得一干二净了。中国的现代史开端之际,似乎也是这样的一个格局,直到1949年才终于达成一个大统一的新中国,所以,中国之大,也就给了许多强梁们占地为王的机会,各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似乎有着由来已久的传统。微缩一点而观之,则可以发现一是农耕经济的长期延漫而造就出的一亩三分地的个体物质价值观,使人人都乐于求田问舍而不肯团结做大,直至做成一个全球化;放大而观之,则是封建之集权,独取天下我一家,以中央高度垄断而谋求天下太平,这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取值最小化,而个人专制权欲追求最大化,因此往往造成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巨大断裂。我想,在中国历史中如果有那么一个时期的社会取经济利益的共同最大化,而又使国家政府权力处于与这个社会利益最大化价值体中的一个适当范围,那么,这个社会或许会在欧洲崛起之先而强盛起来,并可能一直都成为世界的领袖。而连接这个社会利益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则是一个为社会所共同认可并独立存在的法律基础。在后来1776年诞生的美利坚,就采用了这种社会的结构模式,它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
五代之际,中国已演变成了各地军阀以武而争的演习场,成者为王而败者为寇,绝大部分的各代皇帝都是由势力强大的节度使而来。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五代的同时,还有割踞于北方和江南一带的十个小国,这样,大家都济济一堂,成为了中国历史中皇帝最多而时间最短的一个时期。这就有点像中国改革开放中期出现的许多产业投资热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家电行业一下子齐进了数百个牌子,彩电也好、空调也好,各省各地方都有自己的投资企业,最早的彩电大王是四川绵阳的长虹,它甚至打出了“太阳最红长虹最新”的口号,而很快,来自深圳的康佳也以雄厚实力直接对抗,喊出“谁升谁就是太阳”这样的宣言。这场戏只是发生在中国市场经济领域里,但是其势态和作用肌理,与五代十国的节度使们并无两样。在中国,这种以强势夺天下的草头王式的思想,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因为这样的历史,也因为这样的价值观,所以造就了这个社会充分的同质化,以致让所有的一切都如风袭一般,来得快也吹落得快。
我在思考一个关于一个历史的临界值的问题:什么是一个好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是否能够被改变吗?这似乎是一个幼稚甚至无知的问题。然而我在此提出来,其目的无非只是想讨论一下,人类历史或是中国历史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进程中,是否可以由历史的当事人们更趋向人类的理想一些?
作为传统历史观来看,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阶段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既成事实。然而,如果我们将历史活化,会发现,造就这样一段历史社会的客观运动则是一个充满可能的时间和空间力量,并且加上了人类的主体行为,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相互作用的历史肌理中,人类自身的主观作用相对于客观时间与空间的作为就显得更为显要,甚至,这种主观作为可以直接决定历史的方向。基于这种观点,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样的人类历史是我们可以接受或是所期望的,而什么样的历史则难以被我们接受?或者说,当历史以活化的姿态出现在每一个人面前时,我们都有可能进入历史并成为一个历史的参与者和评判者,从而得出对历史的自我看法与结论。一旦如此,我们则因为这样的历史参与而实现对于过往历史的真实审视,以致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拥有一个面对今天和未来的历史态度。这样,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被揭示出来了:什么才会是我们评判历史的真正标准?这个标准将不仅仅用来评判过去,同时更可以用来检省现在与未来将要发生的历史。
裂变:浑沌的能量(5)
在历史之中探索这一标准的实际上大有人在。卢梭在1762年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中专门了讨论了社会的“普遍意志”,他是这样说的:联合起来的几个人只要自视为一个整体,他们就只有一个意志,就是他们共同的生存和普遍的幸福。这时,国家的全部力量既勃发又单一,它的准则既明晰又醒目,没有错综而矛盾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处处都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来。继而,他又说道:只有一种法律从本质上说需要一致的同意,这就是社会契约,因为社会的结合是世界上最自愿的约定,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和自主的,任何人,不论以何种借口,都不能不经他(任何人的对方)的同意而奴役他(任何人的对方)。
可以看到,在这个标准之中,人类社会的契约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将成为标准取值的最重要一部份。这个理由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历史的构成将不因任何个体为标准,而是以人类全社会或国家整体社会为标准。所以,我们必须为历史来建立一条评判的基准线,也可以称之为历史底线,当历史在这条底线之上运行与发展时,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社会普遍认同的评价许可或者是好的评价结果,当历史在更高的取值段位上运行时,我们可以认为它更好或者说符合大部分人类(人类社会共同契约范畴内)的理想;而当历史处于这条底线之下时,我们则会认为它不好或是糟糕。作为衡量标准的这条底线,则必需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最低要求。这个最低要求,也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本要求,既是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平等、自由要求,以及其获得生活与工作并追求幸福的要求。
关于这一要求的讨论,较之于中国传统历史,在欧洲的思想启蒙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还是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前,来自佛罗伦萨的尼科罗。马基雅弗利(1469…1527)就在他所著的《邦主鉴》讨论权力与自由的话题了,他明言阐述了“约制与均衡”的理论学说,指出君主、贵族、平民皆应在邦国的宪法中各占一份,这样便可以“彼此交互约制”。可以观测到,这是欧洲继其漫长的中世纪之后而产生的最早社会的共同利益思想之一,在这个幼稚然而很宝贵的思想探索中,一个进步社会的雏形开始诞生,由君王一统天下的权力正在由贵族和平民所期望共同享有并获得社会性的整体均衡,宪法开始变得趋向独立。这一个阶段中所产生的科学与发现间接地帮到了启蒙思想者们的忙,无论是哥白尼还是开普勒抑或是伽利略和牛顿,他们从另一个方向上破除了君权神授与宗教话语权的传统权威,科学的最早成就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客观世界。这扇门被打开了。
接下来的培根们似乎可以更加轻松地谈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他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这使君王所拥有的最大权力开始动摇。这样,更多的人们开始讨论国家、讨论权力、讨论人类的情感以及善恶与幸福的标准,总之,就在这段历史中,涌现出一大群开始对传统社会与国家甚至君主们进行广泛研讨的人们,并且将他们的言论布散天下。到了笛卡尔的时候,这种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切必须值得“怀疑”,以及对“我”的发现和对思维能力的认识,他干脆把这一些启蒙的思想写在了《宇宙论》、《方法论》、《哲学原理》、《沉思录》甚至有一本叫做《论胚胎的形成》的书中,他热衷科学、数学、几何学、生物学以及哲学等等,如同一个第一次来到迪斯尼乐园的孩子,他想在这个人类发现自身客观存在的新世界之初就了解一切,他甚至为人类发现并创立了坐标系,以此来为平面上任何一个点找到准确的定位(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发现这一坐标系方法对于人类的全部力量和巨大价值),这样,他被视为欧洲近代哲学的始祖。而我看来,这个笛卡尔更是人类近代思想的一位出色向导,直到今天,我们还会感谢他所指引的这条让我们发现自我的人类之路…他的坐标系让我们能够从从容容地找到一个客观存在的自己和时代。
裂变:浑沌的能量(6)
接下来的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则分别从《伦理学》到《单子论》中涉及了人类社会与人本意志与情感的更深层次,甚至莱布尼兹更着重于自由意志的“充足理由原理”,为人的精神站立找到不可置疑的最大理由。而洛克(1632…1704)在英国的出现,可谓是其“光荣革命”时期的思想之旗,他所著的两篇《政治论》,成为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奠基思想。而此际,英国经过“光荣革命”之后尽管仍然采用的是君主制,但这种君主制已不再是君权神授的君主制,而是一种依赖立法裁可、依赖国会的君主立宪制了。自此之后,英格兰银行创立了起来,而自由信教的法令更解除了对人民的迫害,一个重商的资本时代降临了。洛克在他的两篇文章中,说明了国家权力的起源和人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在第一篇文章中批判了传统社会君权神授的统治观点,而在第二篇之中则强调了国家理论与法律理论,他率先提出了天赋人权以及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的国家政治主张,这些思想,在后来美利坚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均获得了充分的表现和继承,并成为今天全球化之下人类共享社会的思想基石。到了1762年,让。雅克。卢梭以一部薄薄的《社会契约论》直接成为了终结传统封建社会的民主思想之宏声,集历史、社会、人类与自然的一切于一身,阐明国家的形成本质是社会契约的产物,而非任何特权与其它,因此,国家的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卢梭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一部著作,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我第一次想写这样一部书,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威尼斯,曾有机会看出,这个被人们如此夸耀的政府,竟有那么多毛病。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么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朗、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
这与我在此想要讨论的那个关于人类历史临界值的问题几乎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这就如同我们在笛卡尔的坐标系中,忽然发现了一些原本就存在而很长时间以来却忽略掉的东西:人类历史的方向究竟应当指向哪里?很显然,21世纪以来的诸多现实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当今天的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在###思想框架下的创新型国家时,当这个政府将这个国家的和谐作为一个关乎民众根本利益的目标时,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去向的最大理由。这是我颇感欣慰,同时也是对这一正在行进中的历史之所以抱着乐观态度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种乐观在1000年前是不存在的,甚至在那之后的很久时间内都不曾真正存在过。自唐之后的所有历史,现在来看,除去一些局部的小小亮点之外,整个中国就像是一架庞大而陈旧的机器,变得越来越笨重,越来越难以运行,最后,她的所有一切都与不断演进的人类历史相脱离(我们不论她是否在某个阶段曾经获得过与世界其它国家或文化的比较),这种脱离是不幸的,然而这种不幸从极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自身所造就的历史所造成的。
我们所谈到的裂变,其客观的作用肌理是带来更多思想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丰富,然而,在中国历史中所发生的诸多裂变则演变成了强权者的争夺与朝代更替。正因为此,这种反复甚至是本质不变的历史使这个国家在十分之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