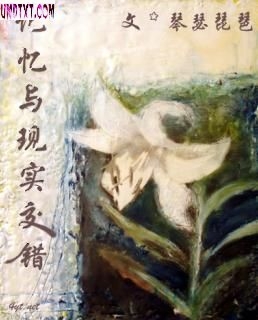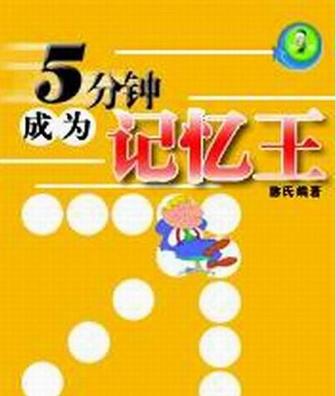香蒲草的记忆-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朋友交往是礼仪上亲,
没名义的男女是露水亲。
有真亲,有假亲,
真正的亲是心上亲,
虚假的亲是嘴上亲。
小时候全靠父母亲,
老了全靠儿女亲。
小子亲,闺女亲,
你要有钱他们亲。
孙子亲,刮地亲,
你没钱他顾不上亲。
年轻时候数谁亲?
恩爱夫妻甜也亲。
吃也亲,看也亲,
白天亲了黑夜亲。
夫妻有缘一世亲,
夫妻无缘更不亲。
这个亲,那个亲,
都是双方互相亲。
父子亲,娘母亲,
兄弟姐妹都是亲。
世上说来数谁亲?
数来数去数母亲。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母亲:我心中的一盏灯
村民的饮食习惯,过去一般是这样的,早晨小米稀饭,玉米窝窝,一碗酸菜。有讲究的人家,另加一碟咸菜,或一碟香椿。在我印象中,香椿是招待客人的好菜。中午一般是喝面条,就是高粱去壳磨成面,再加上榆皮面儿,或切成小块儿,或切成条状。晚上还是以小米稀饭为主,然后将中午剩下的饭菜,放在锅里热上。有些人家也吃小米粥,也吃高梁面搓成的鱼鱼,也吃高梁面蒸成的托托(城里人叫它:发糕)。过去白面和大米很少,或者说纯粹就没有,就连过大年包的那个饺子,都是一半是白面的,一半是高梁面的。并且是,白面饺子还不能吃,为什么?走亲戚还要用啊!
记得我小时候,身体不怎么强壮,经常吃一种形状像圆锥体的驱虫糖块。过几天,随着排泄物出来的,就有许多颜色发白、模样呈长条形的那种东西,医学上好像叫蛔虫。就是现在想起那个东西来,肚里还一阵恶心。那种驱虫糖片又不能经常吃,吃上肚子要疼,不吃肚子也要疼。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母亲就给我檊一小碗白面,切成尖尖形状,倒点醋,放些葱末儿,再切几片鲜姜,连汤带面喝进肚,出一身汗,肚也就不疼了。仿佛那白面儿会治病似的,又好像是我想吃那碗白面儿,有意装出来的病。
过去生活不好是事实,过去人们身体素质,没有任何抵抗力也是事实。就拿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情来说,就足以证明天天吃窝窝头,和天天吃猪肉大米,那绝对是两个概念。况且在那个年代,就是窝窝头也不是你想吃就能吃到的,更何况猪肉白面和大米?
我说得这个事情,就是身上经常起的一种病,医学上的规范名称叫什么?我不知道,村里人都叫它疮。根据疮里流出来的黄水水,又称为黄水疮。过去这疮,一不小心就会长在你的身上。或许是你上火感冒,或许是你不小心碰破一点肉皮,或许是你身上痒,多种情况,同时存在。比如说你身上发痒,你一挖,第二天,你挖过的地方,就会起来一种小水泡。当时你会不以为然,过不了几天,你会看见那个玩意儿一天比一天大,又一天比一天痒,而且小水泡的顶顶上还有颜色。父母一看,才知道起了疮。然后赶紧吃药,然后赶紧打针。这种病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当时吃上药,并不可能一天就好。你就心急,心越急越上火,火越大,疮也就越大。你又怕误了上学,况且上了学,别的同学还说那疮会传染。你只好呆在家里,等疮好,等病好。现在很少有人生疮,或者说,绝对没有,主要原因就是营养的因素,生活的因素。
由吃饭,也由身上那种疮,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那个不像年代的岁月,留给母亲太多太多的灾难,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真有“眼不见、心不烦”之感。好在寒冬过去,就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如今,母亲已步入年迈,和父亲种着几亩地,算是锻炼身体;农闲时,和村里人玩几圈麻将,也算是锻炼身体的一种形状。五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好不好,自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贫困。算不上小康水平,也能说是小富家庭,这是父母引以为豪的。
母亲名讳邢利贞,生于一九四三年农历七月二十二,属羊,那年是民国三十二年。她老人家三岁跟父亲定亲,九岁父亡,跟她祖母一起生活。在东北工作的三老舅舅,给母亲寄回二十块钱来,让她老人家继续念书。母亲也有志气,居然考上白石高小。后来又考上忻定师范学校,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这所学校就让政府给解散了,母亲只好返乡劳动。
母亲十八岁那年,也就是一九六零年农历六月十六这天,她老人家和父亲拜堂成亲。父母结婚四十五年(至二零零五年)了,他俩的感情生活,应该是很完美的。父亲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母亲性格活泼,心直口快,富有正义感。这种性格上的差异,正好形成日常生活上的互补。当然,夫妻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争争吵吵,也是因为那个贫穷的年代,也是为了这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小时候,我见过父母两三次吵架。母亲嘴多,父亲言短,只好躲出去,这时候母亲也就没办法了。事后,母亲一想,原来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主动承认错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只好在生活上表示表示。
这就是我的母亲。嘴上藏不住话儿,为此也得罪过一些人,包括她老人家的五个子女。只要和她老人家相处长了,知道她就是这么个脾气,就是这么个性格,人们也就不会怪她了,反而觉得她这个人实在,好相处。
母亲今年(指二零零五年)六十三岁,一九六九年发生在她老人家身上的那件事情,和疮有关,令人难忘:那年母亲正好逢九年,也就是说,母亲那年二十七岁。母亲身体向来健壮,跟运动员似的,可就是因为劳累过度,生活贫困,营养不良,不知怎么就长起了疮,浑身没有一处完整的皮肤。头发里,嘴里,都是那种疮。就连血液里面,也有了疮这种成份。那个年代,你就是好好的一个人,生活都很艰难,何况家中还躺着一个病人?
在众多亲戚的帮助下,父亲才把母亲背进了医院。
记得那年春节,父母都在医院,家中只有我和两个妹妹。兄妹三人不知怎样过得那个年?别人家是高高兴兴贴对联,欢天喜地放鞭炮,热热闹闹包饺子,人人穿着新衣服。而我们兄妹三人,第一不会做饭,也不会生火炉,家里没有火,比家外面还冷,房子外面刮着风,肚子又饿。当时没学过“饥寒交迫”这句成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比《国际歌》里的奴隶还要饥寒交迫十倍。
因为冻得受不了,我学着生火炉,拿起柴禾,找不见火柴;找见火柴了,就叫你划不着。脸上的黑道道,和屋子里的烟,还有身上烂衣服的味儿,比讨吃要饭的娃娃都可怜。两位妹妹爬在土坑上哭,饿了,喝几口冷水;哭累了,就躺在坑上睡觉。家里冻得睡也睡不踏实,睡一会儿,就醒来。妹妹们看着我,眼里流着泪;我看着妹妹们,眼里也是流着泪。她们要哭,我不让她们哭。她们不哭了,我眼里的泪却止不住地流下来。
当时舅父在砂厂工作,给太原来的汽车装砂子。一天,他回家时,顺便来看我们兄妹三人。一进门,眼中的情景,真是悲惨,一个大男人能失声痛哭,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要多难受,就有多么难受。舅父临走时,给我们留下五元钱,让我们过年。
舅父回家了,我和妹妹们争着抢着看那五元钱,她们看一会儿,我看一会儿,我们正看着,父亲从城里回来了。我抱着父亲的一条腿哭,两个妹妹抱着父亲另一条腿哭,父亲看着我们一个劲地说:别哭,别哭。他老人家抬着头,不敢低头看我们,我知道他是怕我们看见他眼里的眼泪。
父亲用那五元钱,给我买了一板鞭炮,给妹妹扯了五尺花花布,让姨母给她们做了一身新衣服,还买了一堆年货,我和妹妹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
母亲在忻县医院住了一月多时间,花了不少钱。后来,还是在东北工作的三老舅舅,凭他老人家骑马打天下换来的资本,给母亲买回一种叫“六零六”的特效针,才把母亲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还有豆罗地段医院的一位老中医,名字叫王党全(取其音),他老人家也是母亲的救命恩人。母亲病重期间,到医院,医院不收。医生都说母亲成了这个样子,肯定活不成了,是父亲跪下求医院院长,这才答应收下。病刚好一点,母亲就让父亲办出院手续,为省几个住院费。
回到村里,医生都不敢给母亲打针,害怕传染给他们。是母亲的性命,硬逼得父亲学会了打针……
一想起这些伤心的事情,我的手就发抖,我的心就打颤,不知怎么回事,在我内心突然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同时,在我心里埋下一粒种子,也是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当一名医生:
不为别人,就为母亲。
我那年八岁,大妹妹六岁,二妹妹一岁。
大姑:六个孩子的母亲
大姑:六个孩子的母亲
仔细回想起来,大姑曲折多变的人生经历,足可以写一部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曲直而富有情节,神秘而鲜为人知,既可以折射出那个年代多变的风起云涌,又能反映出一个普通女人,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情感蜕变。
然而,由于年龄的差异,我对大姑的认识,只能停留在一些事物的表面。之所以将大姑单列一篇,是因为她与父亲的血肉关系,也因为她在我懂事时开始,就无私地给予比母爱更加神圣的疼爱,我无法忘记留在内心的这份牵挂。
大姑非凡的人生经历,我以为有书写她的必要。因我年龄与她相差甚远,不可能生活在她那个年代,也不可能深入进她的内心深处,只能将我脑海里的一些零碎记忆,再加上从父辈那儿隐隐约约听到的一些传说,略加整理成文。一家之言,恐有失实。动笔前先生敬意,这倒是真的。
十年前的一天,大姑抛弃了她老人家热爱着的这块土地,抛弃了她老人家牵肠挂肚的子孙,还有相依为命的丈夫,撒手西归,入土为安了。
慈竹当风念有影,
晚萱经雨忆留香。
心想姑母心有缺,
月临中秋月不圆。
这是此时我的心情感受,也是对大姑早年不幸的凭吊怀古与真实表白。
大姑名叫张青鱼,生于一九三一年农历十月初六,属羊,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十日下世,享年六十有六。关于她老人家名字的由来,在这儿还有一个说法,大姑出生不久,就随祖母住在她姥姥家,那时大姑还没有名字。祖母大哥——我叫大老舅舅的,就把他们兄弟姐妹孩子的名字连起来叫:老姨姨名叫弓梅棠,她老人家的儿子最大,起名叫中海。大老舅舅的儿子次之,起名叫中全。老姨姨又添了个女儿,起名叫春鱼。大姑排名老四,所以起名为青鱼。
大姑在我印象中,模样就是那么清瘦:高高的个子,脸上经常挂着心思,很少见她老人家笑过。听父亲说,大姑小时候,也跟祖父上过学、念过书,长大后就在家学做女儿活,准备嫁人。大姑先嫁在白石村一户买卖人家,婆家姓李,有二个儿子,大姑男人为老二,名叫李双林(取其音)。不知什么原因,小俩口感情一直不好,整天不是吵嘴就是打架。大姑的大伯子(大姑男人的哥哥)吸大烟,再好的家庭也招架不住只出不进,没几年功夫,原本可以的一个家庭,让他给吸完了,最后连宅院也变卖为“烟雾”了。大姑公婆去世后,大姑与她男人的感情也到了非离不可的地步。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七日,在祖母之侄弓中正家中,我竟然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纸条:长十六厘米,宽八点四厘米,纸质为旧式宣纸,分四行竖写,为毛笔行书,内容为:
美容出阁日子婿意欲循大利月兹查定十一月初十日及二十日惟此二日均无嫁娶请查此二日能否使用为祷
据二伯伯(弓中正)记忆,此条为祖父亲笔手书。文中“美容”,系大姑在她姥姥家的乳名。后面的婿,显然是祖父在其岳父面前的自称。由此断定,此条写作时间为大姑出嫁白石村之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左右。内容为祖父与祖母之父商定大姑出嫁之吉日,是定十一月初十日,还是定十一月二十日?
有幸看到祖父六十年前亲手书写的纸条,我确实感慨万分。内心惊喜自不必多说,好像祖父他老人家如今就站在我身旁似的……
解放后,大姑终于与她男人“再见”了。然后,大姑与本村邢联壁结为夫妻。听村里人说,他俩是村里第一对自由恋爱的夫妻。在那个时候,大姑能摆脱社会上种种压力,大胆地追求人生幸福,其精神实在可嘉。
大姑在我印象中,属于那种思想复杂、遇事拿得起放不下那类人,这也是瘦人一贯的天性。
大姑生五男一女:大哥名叫邢京生(生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取意为北京出生之意;二哥名叫邢平生(生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取意为北京苹果园出生之意;三哥名叫邢文生(生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取意不知为何;四弟名叫邢瑞生(生于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小名叫四猫,取意同上;五弟名叫邢利生(生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七日),小名叫五猫,取意同上。最小的是女儿,名叫邢喜平,小名叫老喜,我只知道她属猪,生于一九七一年,具体到哪月哪日?我就不知道了。老喜从小长得喜人,也分外懂事,这样的小妹妹,实在叫人喜欢。
就在打发大姑后的第二天晚上,大姑托梦给我,梦中情景,如同古装戏中的一幕:房屋建筑古朴典雅,室内物品陈设一应俱全,似曾相识,又有些陌生。给我的感觉是:这就是大姑生活起居的地方,只可叹房屋无顶,星月就在头顶,却看不见大姑在哪儿?……正想着如此房屋,怎能驱寒避风雪时,我突然醒了。醒后与父母谈及此事,三人睡意全无,泪眼相顾。披衣围灯而坐,一阵悲恸之余,猛然想起大姑灵前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