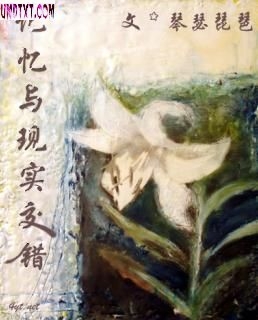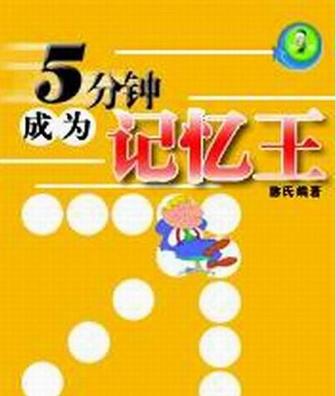香蒲草的记忆-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姑灵前所见“宅院”屋顶扯开一个口子,才意识到大姑托梦并无虚假。清晨起床第一件事情,母亲就是前往大姑夫家,与他老人家讲叙昨晚我在梦中之事。
由此可见,姑侄除过血肉紧密相连,还有虚幻如影的第六感觉存在。这应该是真的。 。。
我的二姑与我的三姑
我的二姑与我的三姑
前面记叙了大姑在我记忆中的几个片断,接着书写一下我的二姑与三姑,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
二姑名叫张全鱼,生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农历是那年的十一月初八,也是民国三十五年,属狗。她老人家名字的由来,照我理解是这样的:二姑之前,祖母已生育二男一女了,加上二姑的到来,应该是尽善尽美的和睦家庭。因此,祖父在二姑名字里,取了一个“全”字。村里人都说二姑年青时,是村里最好看的女孩子,人长得清秀美丽,又有文化,自然要寻一个门当户对的婆家。于是,祖父祖母千挑万选,就将二姑终身托付给了二姑夫。
这个时间应该是一九六九年春天。
二姑夫乃祖母二嫂的侄儿,他老人家名叫王保良(生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农历为那年的十月初四),老家庄磨村,从小随父母居住北京,读书做人品学皆优,于一九六二年考取北京大学地质系。一九六八年毕业后,在宁夏贺兰山从事地质勘探工作,后调回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后来又调回北京国家地质调查局工作,真是踏遍祖国万水千山。虽说二姑年青时随夫在外漂荡,好在晚年定居京城,三个子女亦有所作为,生活舒适平稳,喜庆也就写在脸上。与村里人谈论起北京人的生活,他们普遍认为,在首都工作在首都居住,生活自然不可想象,也正应了祖父取名之寓意。
她老人家生二男一女:女儿名叫王宏(生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农历是那年的十月初四),与二妹春莲同岁,南开大学毕业,现在北京市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属于处级领导干部,目前已是有私家车的小康家庭了。所谓的工作,就是写“准支”两个字。长男名叫王宁(生于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农历是那年的八月初七),也是大学毕业生,现在一家银行工作,还是名字后面带长的那种负责人。次男名叫王宇(生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农历是那年的五月初二),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现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
据母亲回忆,二姑与她老人家还是同班(三班)同学,曾在一个宿舍居住。有些同学已知母亲与二姑之间的关系,除过同学之谊,还有姑嫂之情。有多事人特意让她俩挨住睡觉,可她俩就是“坚守阵地”,即使挨住睡觉,相互也不说话。那时母亲年龄尚小,虽说不懂事,但也知道男女之事,并非人前所言。
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村里过节,也好像是家中某人过生日,总之是喜庆。祖母在家做下好饭,捎话让母亲来。母亲没去有她老人家的原因:终究是没过门的媳妇。人常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公婆婆的。母亲是这样理解的,时机不到,我就是不去。别人也没有办法,就让二姑在大门口等。有些同学知道内中情由,便用激将法来对付母亲:你肯定不敢从寺庄村回家。自然是母亲上当:我就敢。当母亲走到大门口时,二姑从大门里跑出来,扑上去就拉她老人家回家,吓得母亲撒腿就跑。经过这次教训,母亲好长时间不敢走寺庄村,只好绕道而行。
三姑名叫张补鱼,属猴,生于一九五六年农历二月初一。祖母生下三姑后,显然是补来的,因此在她老人家名字里取了一个“补”字。这只是我的猜测。具体详情如何?只有祖父与祖母知道啊!三姑婆家在小豆罗村,在我村东十华里左右。三姑夫名叫寇良田,出身名望家族。
话说至此,不由想起我求学时的一段经历。因为家庭出身因素,自己没有资格去豆罗中学读书,只好在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读书。在此读了二年半左右,于一九七八年春节期间,父母与三姑及三姑夫闲谈起我的学业时,他们建议我转学到豆罗中学。在这中间有个原因,就是三姑夫父亲(我叫黄厚爷爷)与当时豆罗中学校长赵增卯(原平人氏,其长子名叫赵建荣,与我高中同学)关系非同寻常,用村里人的说法就是:能说上话。结果可想而知,我填写了二张试卷之后,就走进了羡慕已久的豆罗中学大门。因学校离三姑家很近,逢时过节,自然少不了要去三姑家“改善生活”。自己参加工作后,假借工作繁忙之理由,看望三姑与三姑夫的时间明显减少。即使有机会,也是来去匆匆。由此说来,这真是我的不忠不孝了,唯有祝福他俩健康长寿。
这应该是我发自内心的祝福。
三位姑妈当中,实在分不清谁最亲我?或者说我最亲谁?姑母亲侄儿,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侄儿孝敬姑妈,也应该是不可否定的一条真理。大姑教给我心胸开阔,二姑教给我勤学多思,三姑教给我任劳无悔。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自身存在的问题。说到感情,我觉得还是二姑对我最亲近也最有感情,这倒不是她老人家有钱的原因,也并非她老人家居住在首都的因素,而是二姑与二姑夫对我的学习进步最为关心。早在我读小学时,二姑夫从外地回来探亲,他老人家给我买了一支钢笔,我像宝贝似地保存着,后来不知怎么就丢了,为此我几天没有吃饭。尤其是恢复高考那年,他老人家专门从北京给我寄回一套《数理化自修丛书》,还有其它一些复习资料。要知道,那时候二姑家的经济也并不宽松。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又是他老人家写信安慰我,在精神上帮助我克服困难。非典那年,儿子考取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二姑与二姑夫显示出来的喜悦之情,比我都那么明显,经济上给予帮助的同时,又亲自送到学校。
所有这些,都是我不应该忘记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外父:有名的好木匠
外父:有名的好木匠
以前村里人喝得都是井水。全村有三四眼水井:异族叔父邢天仓大门东有一眼水井,村西南巷同族兄长张润全房背后有一眼水井,同族伯父张安祥院子里有一眼水井……每天早上一起床,家家男人第一件事情,就是挑起水桶,往水井那儿走,遇到高峰时期,人们还得排队等候。过去的水桶还是木板做成的,形状跟现在的铁桶差不多,只不过木桶是下面底子小,口子大。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有关木匠的。过去衡量一个木匠的水平高不高,技术行不行,一是看他会不会给房做架,二就是看他会不会做水桶。当然,还有许多制作农具活儿,也是衡量一位木匠水平高低的标准。外父就是出了名的好木匠,他家供奉的各路神仙里面,其中就有木匠的始祖:鲁班爷。
外父名讳邢存钱(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也是那年农历的四月初四,属羊,二零零二年农历五月十八下世),在家排行老二,村里人也叫他老人家二存钱。
别得不说,就说我村戏台,那就是他老人家的杰作。过去村里人盖房立架,是一生中的大喜事。请风水先生看日子,选吉时……正式立架那天,还要焚香祭祖,点烛放炮,邀请亲朋好友,好不热闹!那个年代,木匠是很有社会地位的。每到一户人家,村里人实在,吃的是他们平时不吃的好饭,喝的是茶叶,抽的是带把儿的纸烟(村里人对香烟的口头语)。姨夫名讳赵熬元,白石村人,也是木匠,他老人家的师傅,就是外父。小时候,父母还有心思,让我跟姨夫学做木匠活儿,只是后来我考上了学校,错过了求师学艺的机会。过去学个手艺不容易,有个手艺就有一碗饭吃,就会娶媳妇,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由村里人喝水,我想起木匠来,进一步想起我的外父,是因为外父生前对我说过这么二句话:多做有益他人的事情,多做有利于后辈子孙的事情。虽说他老人家是个粗人,但这二句话,却叫我这个自以为有文化的人,经常陷入沉思状态,而不能自拔。
二零零二年农历五月十八这天,一个意外事故,夺取了他老人家的生命,原因应该归于村边的铁路。铁路留给我的悲伤记忆,里面又增添了可恨的一笔。
那年他老人家七十岁,留下二女三男。姐姐年龄最大,生于一九五六年农历六月初十,名梅兰,嫁在西沟村。姐夫姓杨名黄文,生于一九五五年农历八月初十。年轻时姐夫精通机械制造,改革开放那年,他俩在公路旁边办起个汽车修理厂,依靠勤劳,发了家,致了富,生活直奔小康。姐姐生一男一女,儿子名叫杨丽华,小名叫二亲,生于一九八四年农历六月初九,现在重庆工学院读书,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女儿名叫杨午丽,生于一九八零年农历五月初六,小名叫丽丽,读的是医科大学护理专业,现已参加工作,人长得像电视里拍公益广告那位女明星——小男孩端着一盆清水,一边走一边说:妈妈,洗脚。
芳兰为爱人,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出生,农历八月十一,属牛,在家排行第二。为人处事,热情大方,又具有非常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她小时候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没有印象。她给我的记忆,是我俩在豆罗中学上学那会儿。有关我对她的感情,后面单列一篇叙说,在此不提。
对于外父,我是有愧于他老人家的。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对我就像对待玻璃制品那样:小心轻放,切勿倒置。这个形容有些文不对题,但是从另一方面却反映出外父对我是疼爱有加的。他老人家始终没有说过一句令我难堪的话,这可能与他老人家没有文化有些关系。人性的互补,就是这么奇妙:自己瘦,就喜欢与发福的人相处共事;自己爱动,就喜爱个文静羞涩的人。
外父也是如此。其实我又有多少文化呢?可外父就是喜欢,喜欢就是最好的理由。每当我回了村,不管中午,还是早晨,总喜欢和我喝二杯酒,还让外母炒二盘我喜欢吃的菜,边喝边谈他老人家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关于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心情,他老人家总是避而不谈。尽管他老人家不说,可我总觉得他和我说得那些话,说得那些事情,那是用他的话,或者是用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再启发我,再暗示我,再激励我。现在想起那个情景来,就好比日本歌曲《北国之春》里唱得那样:
可曾闲来愁沽酒,
偶尔相对饮几盅?
外父走了。他老人家走了。把家里所有事务留给了外母,留给了三个儿子:长子邢引平(一九*年五月十二日出生),小名叫元林,人实在,不怕受苦受累,有一手爬树的绝活,也是木匠出身,还会鼓捣电玩意儿。娶妻王平,生一子名叫文成。老二名叫邢树平(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出生),小名叫二毛,识文断字,爱看闲书,也是木匠出身。老三名叫邢全平(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出生),小名叫三毛,跟姐姐修汽车,娶妻安三妹,贵州省紫云县人氏,生一男一女,男孩名叫文贵,女孩名叫文英。
外父生前对我讲过他父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我印象极深。由此想起村里人经常说起的一句话:入土为安。何为入土?何为安?据忻州第一才子宋文明解释,入土为安乃人生大事。人一出生,对家庭对社会,都是一种责任。男为人父,承前启后;女为人妇,平衡左右。生为死之开端,死又意味着另一种生命的延续。祖先对人之下世尤其重视,称人亡为“当大事”,人亡后能入土为“当大事”中的幸事。古人又有人死不能入土为遗憾的说法。
外父对我说的这件事情,是关于他父亲的一件往事。外父的父亲名讳邢双根,按爱人的称谓,我亦称他老人家为祖父。我小时候也见过他老人家,个挺高,四方脸,时常穿着整洁。据外父记忆,他老人家在村民中的印象并不勤快,但是他老人家从北路背回他二弟邢双银尸体这件事情,却叫村里人另眼高看。村里人称现在的内蒙为北路,走北路就是去内蒙,走北路跑买卖就是去内蒙做生意。这是村里人那个时期的习惯用语。
关于这件事情的有关细节,据异族叔父邢四福记忆,时间好像是在一九四零年左右,那时日本人还没有打进来。邢双银老人去内蒙做生意之前,家里还有妻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老人家执意要走北路,先在一家商铺当小伙计,后来发展成这家商铺小股东。他老人家在外经商期间,回来过一次,也给家人带回一些钱财,买地盖房,一时成为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就是这么一位老人,不到四十岁就下世了。怎么死的?什么病?家里人甚也不知道。只是有人捎来这么一句话儿,只是捎话的那人说他老人家没有了。再问,那人也不知道。外父的父亲听说后,在怀里揣了一个窝窝头,连夜起程,直奔北路……
可以想象到他老人家,从内蒙背着一副尸体,一步一步又一步,一千里路程有多少步?过草滩,爬雪山,斗恶狼,谁能有此胆略?一步一步往山西走,一步一步往忻州走,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其中艰辛有谁知道?千里背尸图啥?叶落归根应该说是现象,入土为安才是现象后面的本质。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现象尚能理解,本质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啊!由外父想起爱人祖父的一段传奇故事,算是我对他老人家的尊敬。有关千里背尸的事情,在张承志《心灵史》中也有类似的情节。
现在村里人不喝井水了。水井成了历史,井边的辘辘儿,也成了历史上的一幅画面。如今,村里人喝得是自来水,每家院里都安着一个水龙头。方便的同时,也会经常忘记一些本不该忘记的人或事,这是极其不应该的。
外父还说过这么二句话:有理的街道,无理的河道。极其通俗的二句话儿,有着极其深奥的哲学道理。由此可见,有没有文化的标准,并不是多看几本书,或者是会写几个字的因素。大智若